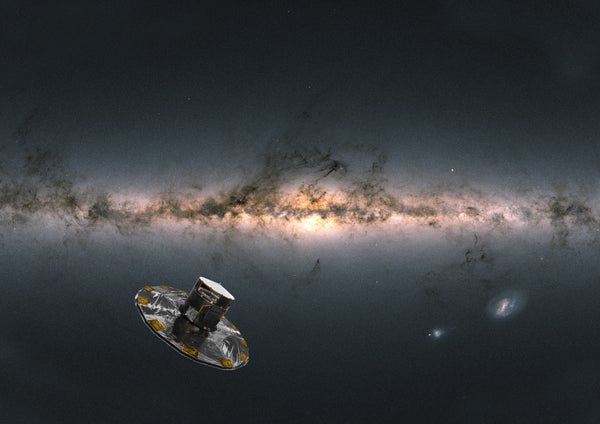6 月 13 日美國東部時間早上 6 點,世界各地的天文學家湧入了蓋亞檔案:這是歐洲航天局 (ESA) 銀河系測繪全球天體測量干涉儀(蓋亞)任務的每一條資料的著陸網頁。經過多年對航天器測量的數億顆恆星的運動、速度、亮度、成分和其他屬性進行校準和驗證,任務官員最終向公眾釋出了資料版本 3 (DR3)。在閱讀新聞稿和在 Twitter 上釋出望遠鏡主題蛋糕的照片之間,科學家們開始在 DR3 中搜尋黑洞、小行星、銀河考古學、系外行星等方面的下一個重大發現。
在釋出後幾分鐘內,歐空局公佈了更新的三維銀河系地圖,併發布了關於我們周圍數十億顆恆星的大量新資訊——它們的組成、執行方向、速度和年齡——所有這些都是為了服務於蓋亞的基本目標,即勘測天空,以便更好地瞭解我們的星系。
“我沒想到我們會有這麼好的覆蓋範圍。所有那些地圖——我的下巴都掉下來了,”義大利國家天體物理研究所都靈天體物理天文臺的天文學家羅納德·德里梅爾說,他也是蓋亞資料處理和分析聯盟 (DPAC) 的成員,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一直從事蓋亞專案。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德里梅爾在釋出前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仔細檢查蓋亞的一些觀測結果——時間剛剛夠整理出一篇論文,這是 DPAC 團隊撰寫的眾多論文之一,以展示 DR3 的可能性。藉助超過 3300 萬顆恆星的三維軌跡的新測量資料(包括它們朝向和遠離我們的運動,而不僅僅是橫跨天空的運動),德里梅爾和他的同事繪製了我們星系不同部分的恆星運動圖,特別是銀河系兩條後緣旋臂和它們之間扁平的棒狀中心。瞭解這些不同區域中的恆星今天的運動方式可以幫助研究人員逆向工程我們星系獨特的螺旋形狀的出現,並瞭解這種結構如何在其他星系中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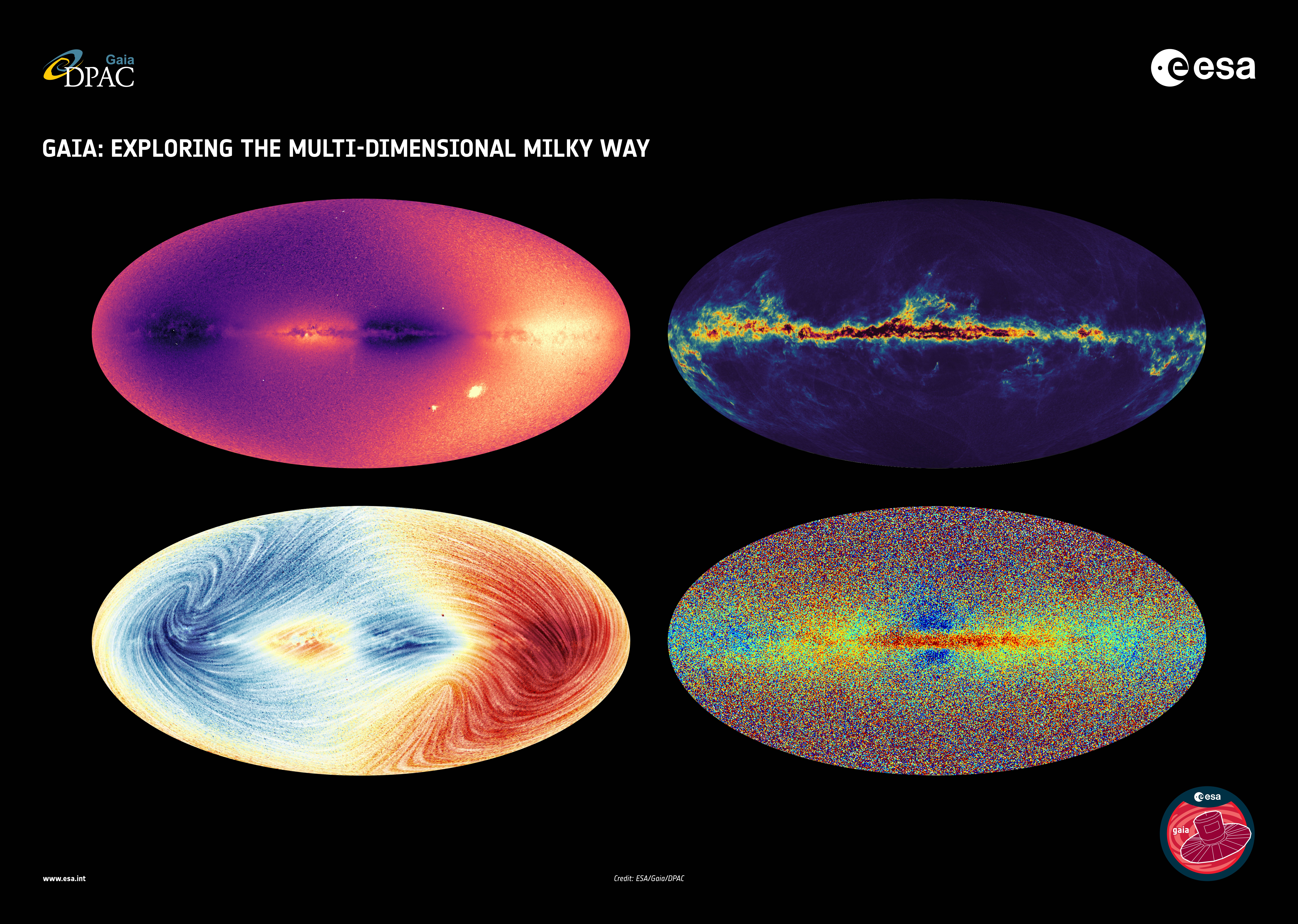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ESA/Gaia/DPAC (CC BY-SA 3.0 IGO)
“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時代,至少對於銀河系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些非常動態的事情正在發生,”紐約市熨斗研究所計算天體物理學中心 (CCA) 的天文學家阿德里安·普萊斯-惠蘭說,他是一篇新論文的合著者,該論文在 DR3 釋出後僅一天釋出到預印本伺服器 arXiv.org 上。他們使用 DR3 中更新的恆星運動來尋找銀河系結構中受到事件干擾的跡象,例如我們與人馬座矮星系之間的近距離接觸——人馬座矮星系是一個小型星系殘餘,被困在我們自身周圍的死亡螺旋中。研究這個和其他“衛星”星系有助於研究人員確定銀河系混亂歷史中的關鍵事件,揭示史詩般的星系間碰撞和近距離接觸,這些碰撞和近距離接觸在數十億年的時間裡產生了我們熟悉的恆星螺旋。“我們星系的歷史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墜落並被銀河系吸收的東西——這既與我們星系的形成有關,也對我們在星系中看到的結構產生影響,”普萊斯-惠蘭解釋道。
蓋亞測量的精確運動也是識別星系內較小規模系統的關鍵,包括雙星,以及圍繞更奇特的天體物理物體(如中子星和黑洞)執行的恆星。這些密集的“恆星遺骸”本質上是大質量恆星死亡後的殘餘物。如果這些大質量恆星位於雙星系統中,天文學家的理論預測,遺骸將繼續圍繞它們尚未死亡的伴星執行,因此研究人員預計很快就會從蓋亞資料中找到雙星中的黑洞。
“我們都對黑洞感到興奮;每個人都渴望找到黑洞,”CCA 的天文學家凱蒂·佈雷維克說。在釋出後的幾天裡梳理了 DR3 中龐大的新雙星系統目錄後,儘管如此,“我們就像,‘真的嗎?什麼都沒有?沒有一個巨大的黑洞在我們尖叫?’ 但沒關係。我們的希望尚未破滅。”
佈雷維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就我認為蓋亞資料將帶來的真正‘動力’科學而言,它只是能夠觀察雙星——質量、種類和演化階段各不相同的雙星,”她說。自資料釋出以來,佈雷維克一直在改進蓋亞雙星系統資料的合成版本。為此,她使用數學模型生成恆星的人工種群,以便最終與真實的蓋亞結果進行比較,從而找出我們當前理論中的漏洞。
恆星的樂趣並不僅限於雙星。“我正在使用 [DR3] 立即做的事情之一是研究一個非常附近的恆星樣本,”紐約市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天體物理學家傑奎琳·法赫蒂說。她希望解開恆星來自哪裡以及未來要去哪裡。DR3 中一個備受期待的新增功能幫助了法赫蒂的工作:恆星光譜,它繪製了恆星亮度如何根據波長或發射光的顏色而變化。光譜傳遞有關恆星溫度和化學成分的資訊。在光譜中識別出的不同元素的指紋可以精確定位可能在同一區域誕生的恆星。這有助於天文學家“倒轉時鐘”,弄清楚各種恆星種群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出現和演化的,同時也暗示了未來會發生什麼,並允許研究預測未來幾代恆星可能在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形成。
但不僅僅是恆星愛好者對光譜感到興奮。DR3 還包含約 60,000 顆小行星的光譜。哈佛-史密森天體物理學中心的費德里卡·斯波託等研究人員可以使用這些光譜來了解遙遠小行星的成分,並找到基於成分的“家族”,以幫助將分散的太空岩石與它們分裂出來的原始物體聯絡起來。斯波託想利用 DR3 對小行星運動的詳細測量以及它們的光譜,回溯小行星的軌跡,以精確定位形成它們的關鍵撞擊事件以及這些事件發生的時間。“如果你沿著整個主[小行星]帶,所有的碰撞,你可以製作一個太陽系早期形成的時間表,”她說。
法赫蒂、德里梅爾、斯波託、普萊斯-惠蘭和佈雷維克都認為,DR3 中有足夠的科學知識供幾代天文學家研究,但這些資料僅來自蓋亞觀測的前 34 個月。隨著任務的繼續,還有多年的未觸及的觀測結果值得期待,天文學家們也知道這一點。“沒有休息,”德里梅爾說,他的 DPAC 團隊的同事自 2021 年底以來一直在研究下一個資料版本。
DPAC 成員兼法國蔚藍海岸天文臺的天文學家保羅·坦加說,到資料版本 4 (DR4)(預計在未來幾年內釋出)時,我們可以預期編目的小行星數量將翻一番。佈雷維克將有更多的大質量恆星可以希望發現周圍的黑洞,並且有更精確的恆星位置和軌跡可供使用,這讓系外行星探險家們感到興奮。
“我們正在檢視蓋亞資料,尋找恆星顯示出受到一顆看不見的大質量行星的拉扯的證據,”美國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莫菲特菲爾德)的天體物理學家塞恩·柯里說。透過使用蓋亞來尋找恆星,這些恆星在其穿過天空的路徑中顯示出明顯的行星引起的擺動,他希望識別出候選恆星系統,以便與其他望遠鏡進行後續研究,從而確認和描述那裡的任何世界。
柯里需要的下一批資料將來自 DR4,但他和他的同事已經確信他們的行星搜尋方法有效,這是基於對早期版本的初步探索——而且他們並不是唯一的人。由特拉維夫大學天文學家阿維亞德·帕納希領導的一個小組在最近被《天文學與天體物理學》接受發表的預印本論文中,證實了在早期蓋亞資料中發現的前兩顆系外行星。熱氣體巨行星 Gaia-1b 和 Gaia-2b 是在它們從地球軌道觀測到的經過各自宿主恆星前方時被發現的,這導致每顆恆星在蓋亞光學器件中的亮度瞬間下降。基於他們的技術的成功——並得到使用地面望遠鏡對行星進行的後續觀測的支援——帕納希和他的同事計劃在新蓋亞資料中搜索相同的亮度變化跡象,以尋找更多的系外行星,這為 DR3 可能進行的活動清單中增加了行星搜尋。
“其他人想要更性感的任務,”法赫蒂說,指的是諸如美國宇航局耗資 100 億美元的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及其類似昂貴的(且規模龐大的)擬議後繼者等專案,這些專案計劃在其他世界中尋找生命跡象。但蓋亞任務的根本性質——對恆星進行全天巡天——是所有天體物理學的基礎。它精確測量亮度以及透過其視線的物體的位置的能力使該任務成為各種天文學的強大通用工具。“這是宇宙的基本測量:距離測量,”法赫蒂說。“這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距離測量天文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