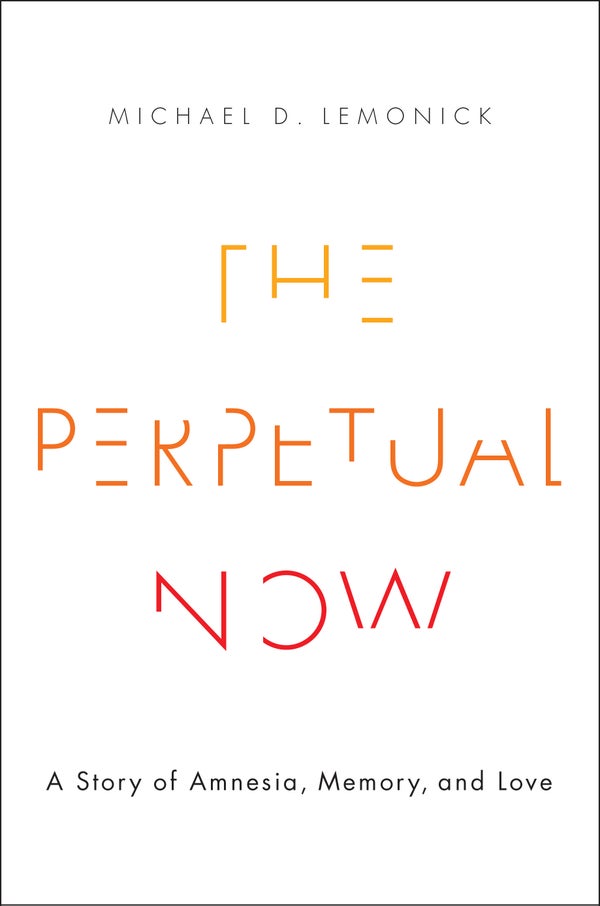節選自《永恆的當下:關於失憶症、記憶和愛的故事》,作者:邁克爾·D·萊蒙尼克。經Doubleday安排出版,Doubleday是Penguin Random House, LLC旗下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集團的一個分支。版權 © 2017 邁克爾·D·萊蒙尼克所有。經許可轉載。
2008年12月5日早上,我從塑膠送報袋裡取出《紐約時報》,展開報紙,讀到頭版頭條:“H.M.,令人難忘的失憶症患者,享年82歲去世。”
對我來說,他當然是令人難忘的。1971年秋天,我在大學一年級的心理學教科書中第一次讀到關於H.M.的報道,當時距離那場剝奪了他大部分現有記憶和形成新記憶能力的實驗性手術還不到二十年。生活在永恆的“當下”的想法似乎令人震驚,我和班上大約兩百名其他學生一起,試圖想象這種存在會是什麼樣子。當然,我失敗了。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作為一名科學記者,每當我寫到涉及記憶科學的故事時,我都會回到H.M.的案例。然而,我從不知道他的名字,這要歸功於布倫達·米爾納和蘇珊娜·科爾金的絕對堅持,這兩位科學家研究了他五十年,在他生前一直保持匿名。但最終,在第七段中出現了他的名字:“星期二晚上5:05,”報道寫道,“亨利·古斯塔夫·莫萊森——在世界範圍內僅被稱為H.M.,以保護他的隱私——因呼吸衰竭在康涅狄格州溫莎洛克斯的一家療養院去世。”
2015年夏天,我坐在蘇珊娜·科爾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辦公室裡,與她談論她與亨利的長期關係,既是作為一名科學家,也是作為他母親去世後他最親近的人。我現在正在撰寫關於朗尼·蘇·約翰遜的文章,她是另一位失憶症患者,病情與莫萊森的非常相似。(約翰遜的母親和姐姐,她的主要照顧者,已決定公開她的全名,以便幫助宣傳對大腦研究的需求)。
我詢問了莫萊森的去世,以及她為了迎接他的離世而計劃了幾十年的屍檢研究。“我們幾乎還沒有開始這項研究,”她說,然後期待地看著我。我茫然地看著她。 “你的下一個問題,”她提示我,“應該是‘為什麼?’” 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什麼?”我困惑地問道。“為什麼,”她繼續說,“七年後,我們對他的大腦細節一無所知?” 現在她提到了,七年似乎確實是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這僅僅代表了科學緩慢而謹慎的過程。
我錯了。
莫萊森去世後,他的遺體立即被送往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在那裡他的大腦被小心地取出並儲存。由於手術記錄、X光片、CAT掃描和MRI,神經科學家和神經解剖學家大致瞭解了他的大腦哪些部分在旨在治癒他頑固性癲癇的手術中被破壞了。外科醫生威廉·斯科維爾切除了亨利海馬體的前部,以及他的大部分內嗅皮層、鼻周皮層和海馬旁皮層,現在這些都被理解為對記憶至關重要。斯科維爾還取出了杏仁核,杏仁核負責處理情緒體驗。
與此同時,廣泛的記憶測試已經探測了他記憶喪失的程度(這是巨大的)。但是,如果不精確地知道取出了多少器官以及哪些器官——以及至關重要的是,他大腦中未觸及的部分在細節上是什麼樣的——科爾金和其他科學家就無法知道他的大腦一開始是否異常。也許他嚴重的癲癇症造成了一些損害,這可能導致了他的記憶問題。
因此,莫萊森的大腦與他的身體輕輕分離,並交給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神經科學家雅科波·安內塞,他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實驗室,專門用於為未來的研究準備它。安內塞明白,儘可能完好地儲存亨利的大腦是多麼重要。“我記得其他著名大腦的不幸命運,”他在一次採訪中告訴我。“你知道愛因斯坦的大腦發生了什麼事,對吧?”
我知道那個離奇的故事。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於1955年去世時,醫院病理學家威廉·哈維取出了大腦,並將其切成兩百多小塊。哈維分發了一些碎片給研究人員,但將大部分碎片放在幾個梅森罐子裡,浸泡在酒精中。他最終去了堪薩斯州威奇托市,記者史蒂文·利維於1978年追蹤到了他。愛因斯坦醃製的大腦仍然在罐子裡,堆在哈維地下室的一堆箱子下面。最終,一些碎片被費城的穆特博物館收藏。您可以在那裡參觀它們,在那裡您還可以看到從小格羅弗·克利夫蘭嘴裡取出的腫瘤;約翰·威爾克斯·布斯胸部的組織切片;著名的連體(“暹羅”)雙胞胎昌和恩·邦克的共享肝臟;以及各種囊腫、腫瘤和畸形。哈維給實際科學家的少數愛因斯坦大腦樣本的研究成果很少,其中一些結果被證明是有問題的。
相比之下,安內塞會將莫萊森的大腦冷凍,然後將其切成兩千多片薄片,每片只有七十微米厚。(一微米等於0.000039英寸;一根人發大約一百微米厚。)然後,科學家們將能夠使用顯微鏡和其他技術觀察這些切片,以精確瞭解大腦的樣子,直到細胞水平。
耗時五十三小時的細緻切片工作(被拍攝和網路直播)幾乎正好發生在莫萊森去世一年後。“大腦切得很好,”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神經科學家大衛·阿馬拉爾告訴我。“這沒有問題。但是……”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從我的科學角度來看,有很多不必要的作秀。” 阿馬拉爾認為,安內塞正在利用這次活動來吸引捐款,以支援他所謂的腦觀測站。該組織網站上寫道:“腦觀測站致力於保持開放科學的最高標準,與其他研究人員和公眾分享我們在實驗室中建立的所有影像和資料。”
然而,至少根據阿馬拉爾和去年去世的科爾金的說法,事情並非完全如此。正如安內塞所承諾的那樣,許多切片被安裝在載玻片上,其餘的則被儲存起來以備將來安裝。但這顯然幾乎就是全部。阿馬拉爾說,通常情況下,像安內塞這樣的科學家會繼續與其他神經科學家建立合作關係,以研究如此有價值的標本。“例如,”他說,“我的專長是海馬體,所以應該聯絡我或像我這樣的人來進行這些研究。” 大腦的其他部分應該由其他專家檢查。但實際上,阿馬拉爾說,“什麼也沒發生,什麼也沒發生,什麼也沒發生。”
科爾金與阿馬拉爾和其他人交談,試圖看看可以做些什麼。“我們試圖干預,”阿馬拉爾說,“但仍然什麼也沒發生。” 科爾金說,安內塞“結果證明是一個糟糕的合作者。他基本上沒有履行他的協議,從而使科學研究戛然而止。” 安內塞確實在2013年在《自然通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描述了亨利大腦的結構性損傷,以及“深部白質中的瀰漫性病變和左眶額皮層中的一個小的、侷限性的病變”。然而,根據被列為該論文合著者的科爾金的說法,這並不等同於完整的病理報告。
安內塞駁斥了這些指責。“令人遺憾的是,”他透過電子郵件說,“一些同事對我在H.M.方面的工作產生了這種印象。多年來,神經病理學檢查的問題已被多次提出,這只是總體計劃工作的一部分,並且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我的善意和促進該過程的具體行動。” 他寫道,在機構層面,“存在許多超出我控制範圍的延誤。我認為,困難是由於未能直接、有效和透明地溝通期望和意圖而引起的。這有時非常令人沮喪,但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在整個過程中對我的特權保持非常開放的態度。” 他說,切割和儲存亨利大腦的所有資金都來自他自己的撥款,沒有任何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或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貢獻。他要求保證腦觀測站在任何科學出版物中都將獲得適當的認可,並且它將在科學中發揮長期作用。“奇怪的是,”他寫道,“我無法獲得合適的回應。事實上,在某個時候之後,我個人幾乎沒有任何回應。”
科爾金並不這麼認為。她說,最終,她只是厭倦了試圖從安內塞那裡撬出資訊。她爭取了麻省理工學院、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管理人員的幫助,以迫使解決問題。最終,高層管理人員同意將亨利的大腦轉移到另一個機構——具體而言,轉移到阿馬拉爾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實驗室。“這花了很長時間來談判,”阿馬拉爾說,“整個過程並沒有得到安內塞博士的促進。”
安內塞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實驗室被關閉了,當我和他通電話時,在我瞭解所有這些背景故事之前,他告訴我他正在尋找資金,為腦觀測站尋找一個新的家。在我聽到科爾金和阿馬拉爾的指責後,我透過電子郵件詢問安內塞,為什麼他的大學同意將亨利的大腦和其他材料的保管權交給另一個實驗室。他並沒有真正回答。“藏品的轉移,”他寫道,“在沒有具體的科學或後勤原因的情況下,是在機構層面經過談判後進行的,這遠遠超出了我的管轄範圍。我於今年 [2015 年] 2 月辭去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職務,因為雖然我尊重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授權領導層認為該解決方案符合大學的最佳利益,但他們的決定最終與我的實驗室和專案的長期成功不符,這些實驗室和專案現在由一個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管理。”
現在大腦已經重新安置,研究終於開始認真進行。阿馬拉爾和他的同事們已經開始數字化安內塞準備的載玻片,建立將在網上釋出的高解析度影像。他們與一位阿馬拉爾稱之為“非常受人尊敬的神經病理學家”的人達成協議,仔細檢查組織中可能導致亨利認知能力下降的疾病。他們已經開始組建幾個專家聯盟,他們將研究大腦的特定部分,試圖精確地瞭解六十多年前莫萊森的記憶製造裝置被破壞時發生了什麼。“我們將能夠提供一個非常明確的描述,”阿馬拉爾說,“關於移除了什麼,完好無損的是什麼。”
就這樣,在 1950 年代開啟現代記憶研究的大腦將為科學做出最後的、至關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