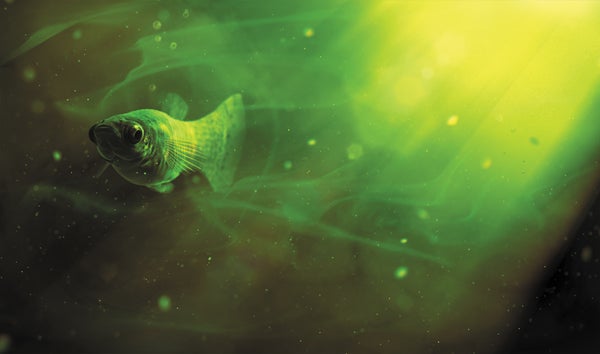九月的一個下午,在墨西哥南部的塔巴斯科州,我們兩人穿過熱帶雨林,朝著流水的聲音走去,為了追尋一種小而重要的魚。 閃亮的藍色大閃蝶在身邊飛舞,吼猴在頭頂的樹上咆哮,為我們從酷熱和潮溼中帶來一絲慰藉。 不久,我們看到一隻翠鳥潛入附近的小溪,然後返回棲木享用它的獵物。 這隻鳥抓住了我們正在尋找的同一種魚:大西洋瑪麗魚(Poecilia mexicana),一種花鱂科魚類的成員,這種魚的雌性直接產下幼魚,雄性則有著鮮豔的色彩,這使得它們在世界各地的水族愛好者中很受歡迎。
有一瞬間,我們渴望地回憶起前幾天在幾公里外的一個地點進行的實地考察,我們在那裡研究了大西洋瑪麗魚,我們將這個地點稱為水晶溪(Arroyo Cristal),因為它有水晶般清澈的水。 那裡的研究令人愉快——我們可以坐在大石頭和木頭上,把腿伸進水中降溫,而我們的研究物件就在我們腳下暢遊。
然而,這一天的實地考察註定會有所不同。 早在我們真正到達目的地之前,空氣中就瀰漫著臭雞蛋的味道,而現在慢慢映入眼簾的水域幾乎不算是清澈。 相反,由於水中懸浮著高濃度的硫顆粒,它們變得渾濁且呈乳白色。 到達水邊後,我們看到所有淹沒在水中的岩石都覆蓋著黏糊糊的硫細菌,而臭水中的許多魚都懸掛在水面,張著嘴,似乎在喘氣。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方式是 訂閱。 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一個新手很難相信我們看到的是前一天在水晶溪觀察到的同一種魚。 畢竟,這裡的棲息地截然不同,這些魚的頭部更大,並且表現出獨特的浮出水面呼吸行為。 但毫無疑問,我們終於到達了今天的實地考察地點:硫磺泉(El Azufre),一條含有天然有毒水平硫化氫(H2S)的小溪,以及已經進化出能夠在其中生存的大西洋瑪麗魚。
富含H2S的環境可以在幾分鐘或幾秒鐘內殺死大多數未適應的生物,包括人類。 鑑於硫化物水的毒性,科學家們長期以來一直對棲息其中的生物著迷,這不足為奇。 事實上,自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研究人員一直在研究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 但在過去的 15 年裡,由於基因組測序技術的進步,使得研究人員能夠在分子水平上了解生物如何適應環境挑戰,因此對這些生物的生態和進化的科學研究激增。 透過將對這些魚類的實地觀察與對其 DNA 的分析相結合,我們和我們的合作者獲得了關於自然選擇(進化的關鍵機制)內在運作方式的迷人新見解。 除了揭開自然選擇的面紗外,這項研究還使科學家能夠探索魚類適應的極限。 掌握這些資訊後,我們或許有一天能夠預測物種在面對汙染和其他人為造成的棲息地改變時的命運。
極端棲息地
花鱂科魚類並不是唯一適應看似不適宜生存的條件的生物。 我們的星球包含各種極端環境——從滾燙的溫泉和高壓深海到鹽沙漠和不見天日的地下洞穴——所有這些環境都孕育著生命形式。 然而,硫化水對生命尤其具有敵意。 硫化氫是一種廣泛存在的有毒物質,它可以透過淡水硫化物泉、海底熱液噴口或沿海泥灘和鹽沼自然進入環境。 天然存在的 H2S 可能源於地質活動,這種活動從地球深處釋放有毒氣體——就像我們在研究的硫化物溪流中發生的那樣——或者源於大量有機物的腐爛。 它也可能作為人類活動的汙染物進入水生環境,例如造紙、皮革鞣製以及天然氣和地熱發電的生產。 即使是極少量的 H2S 也對大多數動物具有劇毒,因為該化合物會結合環境中可自由獲得的氧氣,從而剝奪它們可呼吸的氧氣,並且它會阻止血紅蛋白蛋白的活性,而血紅蛋白蛋白是在血液中運輸氧氣的。 所有這些活動都會導致窒息死亡。 H2S 還會阻止細胞從食物中提取能量的過程。 更糟糕的是,它會自由穿透魚類脆弱的鰓組織中的細胞膜,因此它們不必攝入它也會受到傷害。 人類吸入 H2S 也會有危害風險,因此我們在 H2S 附近的硫化物源附近工作較長時間時,要麼儘量縮短接觸時間,要麼佩戴防護裝備。 毫不奇怪,世界各地水生棲息地中自然和人為脈衝釋放的 H2S 已導致魚類和其他生物的大規模死亡。

墨西哥南部一條名為硫磺泉(El Azufre)的
然而,包括花鱂科魚類所屬的硬骨魚類群(當今海洋和淡水棲息地的主要類群)的各個成員已經適應了環境中的 H2S。 其中一些最有趣的物種,包括蜿蜒的海鱔和比目魚狀的鮃魚,生活在海底的熱液噴口和冷泉周圍。 然而,到達這些動物既困難又昂貴,需要使用堅固的潛水器,這排除了我們感興趣的大部分實驗工作。 因此,我們自己的研究重點是更容易接近的花鱂科魚類,特別是超過 10 種不同的瑪麗魚、孔雀魚、劍尾魚和食蚊魚,它們獨立地在整個新世界的小溪流和河流中定居了數十個有毒的硫化物泉。
應對機制
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已經進化出許多特徵,使它們能夠在有毒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其中一些特徵是行為上的。 例如,為了應對硫化物水中低氧的可用性,這些魚類會在水面附近花費大量時間,在那裡它們可以利用水柱中含氧量更高的最頂層。 (儘管進行這種所謂的表面呼吸的魚類看起來像是在吞嚥空氣,但它們實際上並不能那樣做。 相反,它們吞嚥的是富含氧氣的水。)這種行為是有代價的,因為它限制了其他活動(如覓食)的時間,但它有助於它們獲得所需的氧氣。
這些有毒水中有限的氧氣供應也塑造了這些魚類的身體特徵。 最引人注目的是,硫磺泉種群的頭部明顯比來自非硫化物棲息地的同類更大。 頭部的這種擴大源於鰓區域的擴張,這有助於魚類吸入更多的氧氣。 一種特殊的適應硫化物的物種,硫磺瑪麗魚(Poecilia sulphuraria),是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和恰帕斯州少數幾個硫磺泉特有的物種,也進化出了奇特的下唇附屬物,以進一步幫助氧氣攝入。 在全球各地各種低氧環境中的非花鱂科魚類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突起,並且人們認為這些突起透過擴大口腔區域的表面積來促進撇取最上層水位的氧氣。
除了進化出增強氧氣攝入的特徵外,生活在硫磺泉中的魚類還經歷了有助於它們解毒 H2S 的適應。 所有動物都會產生一種名為硫化物:醌氧化還原酶 (SQR) 的酶,這種酶允許它們透過與 H2S 結合並形成無毒化合物來解毒極低濃度的 H2S。 但是,一旦有毒物質的濃度變得太高,就像硫磺泉中發生的那樣,酶就無法捕獲所有有毒物質,多餘的有毒物質就會開始干擾細胞產生能量的能力。 我們的魚類已經進化出對 SQR 通路的修飾,使其能夠在更高濃度的 H2S 下進行解毒。
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產下的幼魚也比棲息在無毒環境中的同類大得多。 儘管幼魚的體型較大意味著魚類的後代較少,但這種策略對於它們的環境條件來說是有意義的。 體積的增加會導致體積的更大增加,相對於表面積的較小增加。 因此,稍微大一點的後代將具有更高的體積與表面積之比。 這種安排是有益的,因為它使更多的身體組織可用於解毒進入的 H2S,同時僅略微增加暴露於毒素的身體表面。
關於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也許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們具有許多相同的適應性。 我們發現,與生活在周圍無硫化物水域的祖先相比,各個物種和地理區域的硫化物種群都進化出了相同的新特徵。
這些獨立的適應硫化物的魚類譜系之間的高度相似性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反覆獨立地適應 H2S 的花鱂科魚類種群在進化其共同的適應性特徵時,是否經歷了相同的 DNA 變化,還是它們透過不同的分子途徑獲得了這些特徵? 為了找出答案,我們與德國法蘭克福生物多樣性和氣候研究中心的馬庫斯·芬寧格(Markus Pfenninger)以及其他幾位同事合作。 我們分析了來自兩個種群對的數百條大西洋瑪麗魚的 DNA——每對種群都由一個適應硫化物的群體及其未適應的祖先組成——來自墨西哥南部的兩條平行河流流域。 (同一個河流流域可以同時擁有富含硫化物和無硫化物的支流。)統計方法使我們能夠推斷出整個基因組中任何給定基因存在多少變異。 它們還使我們能夠確定哪些變異顯示出被自然選擇驅動到這些種群中的高頻率的跡象——也就是說,透過幫助生存和繁殖——而不是透過偶然機會變得豐富。
我們發現,一個適應硫磺的種群中的基因組變化往往是該種群獨有的,而與其他種群不共享。 然後,我們透過一個數據庫運行了兩個適應硫化物的種群之間存在差異的基因,該資料庫列出了各種基因的功能和相互作用。 事實證明,即使已被改變的確切基因因種群而異,但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參與了相同所謂的代謝途徑的調節——支援生命的化學反應。 (這裡的代謝不僅指魚類如何燃燒食物中的能量,還指生化機制中不同蛋白質為維持其生命而採取的行動,這可能涉及各種適應。)然後,我們的資料表明,存在許多遺傳途徑可以進化出對環境壓力源的相似適應性。

來源:製圖專家(地圖);吉莉安·沃爾特斯(Jillian Walters)(插圖);來源:“H2S 耐受魚類 Cox 基因的平行進化是適應有毒環境的關鍵”,馬庫斯·芬寧格等人,《自然通訊》第 5 卷,文章編號:3873。線上釋出於 2014 年 5 月 12 日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喬安娜·凱利(Joanna Kelley)、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邁克爾·託布勒(Michael Tobler)及其同事最近的一項研究進一步支援了這一觀點。 他們發現,在墨西哥南部適應硫化物的大西洋瑪麗魚種群中,基因表達模式(使用基因製造蛋白質和某些其他分子)因種群而異。 但是,參與調節代謝途徑的基因的表達在所有方面都大致升高到相同的程度。 這種基因活動模式反映了我們在基因序列本身中看到的情況:魚類遵循了不同的分子途徑,以獲得解決在有毒水中生存問題的相同解決方案。
對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的研究也關係到進化生物學的另一個基本問題。 儘管一些專家認為,暴露於相同壓力源的種群應該經歷相當相似的進化變化,但另一些專家認為,確切的進化順序可能會影響結果。 後一種想法背後的思路是,如果某些隨機出現的突變代表關鍵的適應性,那麼它們應該在各自適應硫化物的種群中迅速傳播。 不同的初始關鍵適應性可能會透過改變後期出現的突變的選型優勢來影響給定種群的後續進化軌跡。 我們的結果支援了這種觀點。 我們研究了三個適應硫化物的的大西洋瑪麗魚種群,發現其中兩個種群的硫化物抗性是在一個製造稱為細胞色素 c 氧化酶 (COX) 的關鍵蛋白質的基因中進化而來的,該基因參與產生細胞的主要能量來源。 第三個種群沒有獲得這種初始關鍵適應性,不得不提出另一種進化解決方案來保護其能量產生過程免受有毒硫化物的侵害。
進化的溫床
殖民如此可怕的環境的挑戰是如此艱鉅,以至於人們可能會合理地懷疑,為什麼自然選擇會偏愛這種冒險行為。 但有一個主要的優勢:缺乏大多數其他物種,包括其他魚類捕食者和食物競爭者。 例如,在墨西哥南部的硫化物溪流中,只能發現專門的花鱂科魚類——周圍水域中大量的其他魚類都不存在。
事實上,儘管這些硫化物水域令人望而生畏,但它們實際上可能會促進而不是扼殺新生命形式的進化。 在物種形成的傳統觀點中,地理障礙對以前相連的種群進行長期隔離,使得種群能夠沿著自己的進化軌跡進化,直到它們彼此之間變得非常不同,以至於它們可以被歸類為不同的物種。 但是,生物學家正在發現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即使在沒有此類障礙的情況下,適應不同的生態條件也可以促進物種形成。 對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的觀察證實了這種情況。
我們發現,適應一種棲息地型別(無論是硫化物還是非硫化物)限制了魚類自由移動到另一種棲息地型別的潛力。 這種形式的自然選擇基本上導致適應硫化物的魚類僅出現在硫化物地點,反之亦然,即使這兩個棲息地之間僅相隔幾十到幾百米。
其他因素在這些系統中產生和維持生殖隔離也很重要,例如捕食(不適應的個體更容易成為捕食者的受害者)。 如果棲息地之間確實發生遷徙,或者如果不同種群(稱為生態型)的成員在硫化物和非硫化物棲息地之間的混合區相遇,則這些魚類不會雜交繁殖。 交配選擇實驗表明,非硫化物水域中的雌性更喜歡與自己生態型的雄性交配。 雌性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現出這種偏好似乎取決於自然選擇的強度:我們發現,當針對遷徙的適應硫化物雄性的自然選擇較弱時,雌性對其自身生態型的偏好更強。 似乎當雌性更有可能遇到外來雄性時——從而產生不適合的雜交後代——它們就會進化出對外來者的更強烈的厭惡感。 相反,當針對遷徙者的自然選擇很強,因此遇到它們的可能性很低時,雌性不太可能進化出對外來雄性的厭惡感。
在適應硫磺泉的同時進化出新物種的花鱂科魚類的確切數量尚不確定,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尚不清楚遺傳分化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或者與鄰近種群的雜交繁殖是否仍在發生。 但是,一些表現出所有這些適應性的適應硫化物的譜系大約有 10 萬年的歷史——在進化術語中相當年輕。 它們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進化出其獨特的特徵,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與無毒水域鄰居的生殖隔離,這暗示硫化物水域的極端條件實際上可能會加速物種形成。 我們最近的一項研究支援了這一觀點。 我們發現,適應硫化物的花鱂科魚類的生殖隔離程度與每個生態系統中 H2S 毒性的濃度直接相關。
如果花鱂科魚類能夠快速進化出對天然毒物的適應性,那麼它們是否能夠適應人為活動的有毒汙染呢? 康涅狄格大學的諾亞·裡德(Noah Reid)及其同事去年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來自北美汙染地點的鱂魚(雖然與花鱂科魚類屬於不同的科,但與花鱂科魚類有關)能夠反覆快速地進化適應工業綜合體的有毒汙染。 作者認為,這可能是鱂魚體記憶體在大量遺傳變異的結果,這為它們提供了大量的預先存在的遺傳工具,以便在適應來自汙染的新選擇壓力時“選擇”。 花鱂科魚類是否也具備類似的條件尚不完全清楚,儘管我們的研究表明,新的 DNA 突變對這些魚類比現有的遺傳變異更重要。 但是,鱂魚的研究和我們自己的發現似乎都表明,至少一些相對較小且壽命短、每年繁殖幾代的魚類,在某些條件下,甚至可能能夠適應人為活動造成的一些劇烈的環境變化。
許多問題仍然存在。 例如,我們尚不瞭解為什麼 H2S 的存在在某些生態系統中導致了可預測的適應性和生殖隔離,而在另一些生態系統中卻沒有。 但是 DNA 測序技術正在迅速改進,成本正在穩步下降。 鑑於這些趨勢,以及最近釋出的幾種花鱂科魚類的基因組,我們預計很快將在我們對管理這些致命水域中共同和獨特進化模式的遺傳機制的理解方面取得巨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