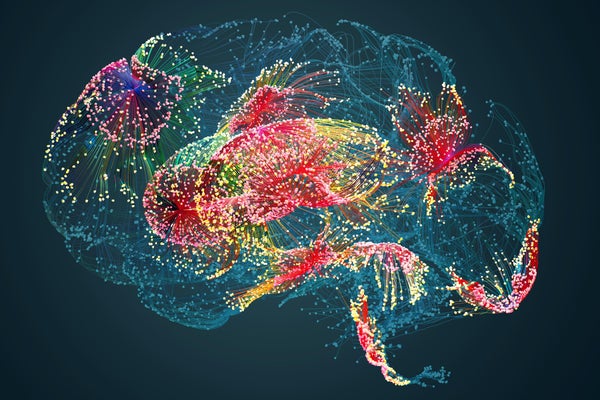大腦只是浩瀚宇宙中的一件傢俱,受制於與小行星、電子或光子相同的物理定律。從表面上看,其三磅重的神經組織似乎與量子力學幾乎沒有關係,量子力學是所有物理系統的教科書理論基礎,因為量子效應在微觀尺度上最為明顯。然而,新提出的實驗有望彌合微觀和宏觀系統(如大腦)之間的差距,併為意識之謎提供答案。
量子力學解釋了一系列無法用日常經驗形成的直覺來理解的現象。回想一下薛定諤的貓思想實驗,其中貓存在於疊加態中,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似乎沒有這種不確定性——貓要麼是死的,要麼是活的。但量子力學方程告訴我們,在任何時刻,世界都由許多這樣的共存狀態組成,這種張力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物理學家。
宇宙學家羅傑·彭羅斯在 1989 年大膽地提出,每當疊加的量子態坍縮時,就會發生一個意識瞬間。意識的起源和量子力學中所謂的波函式坍縮這兩個基本的科學謎團是相關的,這一想法引發了巨大的興奮。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當今塑造我們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彭羅斯的理論可以建立在量子計算的複雜性之上。考慮一個量子位元,即量子資訊理論中的資訊單位,它存在於邏輯 0 和邏輯 1 的疊加態中。根據彭羅斯的說法,當這個系統坍縮成 0 或 1 時,就會產生一個意識體驗的閃爍,用一個經典的位元來描述。
彭羅斯與麻醉學家斯圖爾特·哈梅羅夫共同提出,這種坍縮發生在微管中,微管是管狀的細長結構蛋白,構成細胞骨架的一部分,例如構成中樞神經系統的細胞。
這些想法從未被科學界採納,因為大腦是潮溼和溫暖的,不利於疊加態的形成,至少與現有的量子計算機相比是這樣,現有的量子計算機在比室溫低 10,000 倍的溫度下執行,以避免破壞疊加態。
當應用於兩個或多個糾纏的量子位元時,彭羅斯的提議存在缺陷。測量其中一個糾纏的量子位元會立即揭示另一個量子位元的狀態,無論它們相距多遠。它們的狀態是相關的,但相關性不是因果關係,並且根據標準量子力學,糾纏不能用於實現超光速通訊。然而,根據彭羅斯的提議,參與糾纏態的量子位元共享一種意識體驗。當其中一個量子位元呈現確定的狀態時,我們可以利用它來建立一個能夠以超光速傳輸資訊的通訊通道,這違反了狹義相對論。
我們認為,數百個量子位元(如果不是數千個或更多)的糾纏對於充分描述任何一個主觀體驗的現象學豐富性至關重要:顏色、運動、紋理、氣味、聲音、身體感覺、情感、思想、記憶碎片等等,這些構成了生命本身的感受。
在我們和同事發表在開放獲取期刊Entropy上的一篇文章中,我們顛倒了彭羅斯的假設,提出每當系統進入量子疊加態時,而不是坍縮時,就會產生體驗。根據我們的提議,任何進入具有一個或多個糾纏疊加量子位元的狀態的系統都將體驗到意識的瞬間。
聰明的讀者,您現在肯定在對自己說:但是等一下——我從不有意識地體驗疊加態。任何一種體驗都具有明確的品質;它是一回事而不是另一回事。我看到一種特定的紅色陰影,感覺到牙痛。我不會同時體驗紅色和非紅色,疼痛和非疼痛。
任何意識體驗的確定性自然而然地出現在量子力學的多世界解釋中。多世界觀點是物理學家休·埃弗雷特在 1957 年首次提出的形而上學立場,它將時間的演化視為一棵巨大的分支樹,量子事件的每一種可能結果都會分裂出自己的宇宙。一個進入疊加態的量子位元會誕生兩個宇宙,其中一個宇宙中量子位元的狀態為 0,而在孿生宇宙中,除了量子位元的狀態為 1 之外,一切都相同。
糾纏可能為腦科學家提供其他東西,因為它為所謂的繫結問題提供了一個自然的解決方案,即每種體驗的主觀統一性,長期以來,這種統一性一直對意識研究構成關鍵挑戰。考慮一下看到自由女神像:她的臉、頭上的皇冠、她舉起的右手上的火炬等等。所有這些區別和關係都結合成一個單一的感知,其基質可能是許多相互糾纏的量子位元。
為了使這些深奧的想法具體化,我們提出了三個實驗,這些實驗將越來越多地塑造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第一個實驗,目前正在進行中,這要歸功於位於聖莫尼卡的 Tiny Blue Dot 基金會的資助,旨在為量子力學與神經科學的相關性提供證據,這兩個非常容易接近的試驗平臺:微小的果蠅和大腦類器官,後者是由人類誘導的多能幹細胞生長而成的數千個神經元的扁豆大小的集合體。眾所周知,惰性氣體氙氣可以在動物和人身上充當麻醉劑。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一項實驗聲稱,其麻醉效力(以誘導動物無法移動的氣體濃度衡量)取決於氙氣的特定同位素。元素的兩種同位素包含相同數量的帶正電的質子,但原子核中包含不同數量的不帶電的中子。同位素的化學性質(即它們與什麼相互作用)大致相似,即使它們的質量和磁性略有不同。
如果果蠅和類器官可以用來檢測不同的氙同位素,那麼我們將開始尋找惰性氣體(並且與蛋白質或其他分子結合保持疏遠)實現這一目標的精確機制。是這些同位素的質量(131 個核子與 132 個核子)的微小差異造成了差異嗎?還是它們的核自旋,原子核的量子力學性質?這些氙同位素的核自旋差異很大;有些同位素的自旋為零,另一些同位素的自旋為 1/2 或 3/2。
這些氙實驗將為第二個後續實驗提供資訊,在第二個後續實驗中,我們將嘗試將量子位元耦合到大腦類器官,從而使糾纏在生物量子位元和技術量子位元之間傳播。最終的實驗(目前仍純粹是概念性的)旨在透過以糾纏的方式將工程量子態耦合到人腦來增強意識。然後,人可能會體驗到擴充套件的意識狀態,就像在服用死藤水或裸蓋菇素的影響下所訪問的狀態一樣。
量子工程和腦機介面的設計都在快速發展。利用量子科學和技術直接探測和擴充套件我們的意識思維可能並非超出人類的創造力。
這是一篇觀點和分析文章,作者或作者表達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