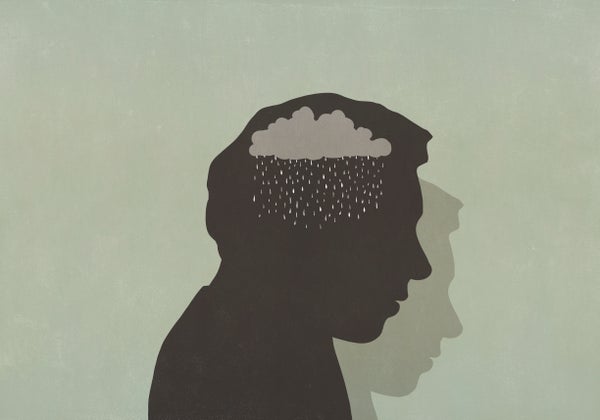近年來,人們普遍認為,心理療法——特別是認知行為療法 (CBT)——在治療抑鬱症方面與百憂解和來士普等藥物的效果相當。單獨使用或兩者結合使用有時可以緩解這種情緒障礙。在更仔細地審視這兩種療法後,CBT——它深入研究功能失調的思維模式——可能具有一種益處,使其成為患者更好的選擇。
原因可能根植於我們遙遠的進化史。學者們認為,人類可能會患上抑鬱症,以幫助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可能導致某人與家人、朋友、氏族或更大的社會脫節的問題上——這種被排斥的地位,特別是在舊石器時代,幾乎意味著必然的悲慘命運。按照這種說法,抑鬱症的出現是一種情緒狀態,使我們長期而認真地思考那些可能導致我們變得沮喪的行為,因為我們生活中的某些問題在社會上是有問題的。
最近發表在《美國心理學家》上的一篇文章,該雜誌是美國心理學會的旗艦出版物,權衡了抑鬱症可能的進化起源對於關於心理療法與抗抑鬱藥的優點的爭論可能意味著什麼。在文章中,範德堡大學心理學教授史蒂文·D·霍隆探討了幫助患者理解抑鬱症潛在原因的意義——這是CBT的目標,也符合進化的解釋。相比之下,抗抑鬱藥的鎮痛效果可能會轉移患者的注意力,使其無法進行抑鬱症進化的反思過程——這也許是心理療法似乎比抗抑鬱藥產生更持久效果的原因。《大眾科學》與霍隆談論了他對這個話題的看法。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以下是經過編輯的採訪稿]。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描述了一種觀點,即人類進化出一種抑鬱傾向,作為恢復情緒和心理平衡的一種手段。這使人們能夠良好地融入他們的社會環境。那麼,您能解釋一下抑鬱症如何成為進化的產物,實際上可以保護我們嗎?
在 2000 年代後期,我讀了進化生物學家保羅·安德魯斯的一篇論文。它寫得非常出色,考慮周全——但我完全不同意。主要前提是抑鬱症是一種進化適應,旨在使人們進行反芻思考。
您為什麼不同意?
對於臨床醫生來說,我們認為反芻思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充其量是抑鬱症的一種症狀,最壞的情況會導致抑鬱症加深。我們一直認為它是一種尾氣管排出的廢氣,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幫助。
但安德魯斯和他的同事 J. 安德魯(安迪)·湯姆森回顧說,在我們的進化史上,讓你感到抑鬱的是某種重大問題——很可能是一個社會問題——這可能會讓你被部落排斥。而你必須做的是坐下來思考問題。
我們大多數人都可以認為焦慮是一種有用的功能,因為焦慮使我們遠離危險。它來得很快,很迅速,就像你在樹林裡踩到一條可能有毒的蛇後發生的反應。但大多數人並不認為抑鬱症有任何功能。它只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東西。訣竅是要弄清楚抑鬱症的目的是什麼——當安德魯斯和湯姆森觀察到當你感到抑鬱時會發生什麼時,他們發現大量的能量流向了大腦。
其原因是幫助我們更仔細地思考出錯的事情,首先要了解原因是什麼。這回答了這個問題:我為什麼感覺這麼糟糕?第二件事是:我如何才能出色地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
所以,你不需要在抑鬱症中迅速行動;糟糕的事情已經發生了。你不必躲開毒蛇或豹子。但你確實必須解決一些複雜的社會問題,而反芻思考可以幫助你實現目標。因此,反芻思考與其說是抑鬱症令人不快的副產品,不如說是抑鬱症進化的真正原因。它可以幫助你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
您似乎現在認可了安德魯斯和湯姆森的觀點。這種思路實際上如何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作用?抑鬱症和需要反芻思考的社會問題在什麼時候開始出現?
這些複雜的社會問題通常在青春期開始出現,那時年輕人開始問:我會有男朋友和女朋友嗎?我如何才能讓男孩或女孩喜歡我?我在學校表現會好嗎?我的父母對我滿意嗎?我能上大學嗎?我能找到工作嗎?
您在心理療法——特別是認知行為療法——方面的專業知識與抑鬱症的進化理論如何結合?
在這種背景下,認知療法變得有點自然而然。它教導人們如何更有效地進行反芻思考。認知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會抑鬱,是因為他們對自身抱有不準確的信念。這可以與人們可能會陷入困境的附加概念相結合。例如,如果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就會開始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一個失敗者。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抑鬱症會促使他們更認真地思考問題的根源以及他們可以應用的解決方案。在大多數情況下,在我們祖先的過去,這都運作良好;即使在沒有治療的情況下,大多數抑鬱症也會自發緩解。認知療法至少可以加快這一過程,最多可以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個體擺脫困境,他們通常對自己的個人能力或可愛程度做出負面評價。
解決方案本質上是教他們科學方法,以便他們擺脫困境。我們要求患者問自己:你認為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還有哪些其他解釋?支援這種或那種解釋的證據是什麼?特別是,我們鼓勵那些陷入困境的患者將他們所謂的穩定特質理論——“我無能”或“我不可愛”——與更具行為性的解釋進行比較:“我選擇了錯誤的策略。”
您研究的一個領域是 CBT 是否比藥物具有更持久的效果,您對這如何為抑鬱症的進化基礎提供證據感興趣。
基本上,我們有充分的臨床證據表明,認知療法在短期內至少與藥物一樣有效,並且在長期內更持久。CBT 可以讓人們認真思考他們的問題,從而有助於達成解決方案,而藥物可能只是麻痺抑鬱症的潛在壓力。
您打算以某種方式檢驗這個想法嗎?
我在越南有同事,他們對我們想做的一項研究非常感興趣,在該研究中,我們將接受 CBT 治療康復的人與接受藥物治療康復的人進行比較——並將這些與使用中草藥的對照組進行比較,中草藥在那裡被廣泛認為有效。如果抗抑鬱藥確實以惡化抑鬱症潛在病程的方式抑制症狀,那麼當我們停止使用藥物時,這些患者比我們停止使用中草藥時更可能復發。如果 CBT 確實具有持久的效果,可以預防抑鬱症,那麼接受治療康復的患者在治療結束後復發的可能性應該低於接受中草藥康復的患者。本質上,中草藥充當理想的非特異性對照,因為它既不提供認知療法中教授的應對技巧,也不提供抗抑鬱藥提供的藥理活性血清素相關成分。我們有一項我們想做的試驗應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尚未完成。
不過,沿著這些思路是否已經存在一些證據?
有超過六項研究表明,接受認知療法治療以達到緩解的患者在治療結束後復發的可能性低於接受抗抑鬱藥物治療以達到緩解的患者——並且有兩項研究表明,這種持久的效果可能延伸到預防復發。我們不知道所有這些在擬議的進化背景下如何適用:認知療法是否具有持久的效果,或者抗抑鬱藥物是否可能不利於延長潛在的發作時間——正如進化理論所暗示的那樣。需要的是一種非特異性對照,既沒有持久的效果,也沒有藥物引起的麻醉效果。認知療法是否真的具有持久的效果,或者抗抑鬱藥物是否具有不利影響,仍有待確定。將每種療法與中草藥等非特異性對照進行比較,應該可以讓我們絕對地確定哪種情況是哪種。
您談到了試圖衡量這類試驗中是否真的存在持久效果的困難。
認知療法(相對於抗抑鬱藥)觀察到的持久效果也可能與臨床試驗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有關。儘管我們在試驗開始時將患者隨機分配到認知療法組或抗抑鬱藥組,但由於損耗,我們通常會損失約 15% 的樣本,另有 25% 的樣本對任何一種干預措施均無反應。這意味著最初隨機分配的樣本中只有約 60% 進入了後續複發率比較。如果不同型別的患者對認知療法的緩解與對抗抑鬱藥的緩解不同,則可能會使任何後續比較產生偏差。
您認為這些關於 CBT 的見解會對重度抑鬱症產生影響嗎?
我不知道,也不一定認為它們會產生影響。對於精神病性抑鬱症,您會首先選擇電休克療法。我不確定分析性反芻思考假設是否適用於精神病性抑鬱症,或者是否需要適用。對於每一種進化適應,都存在機制進化崩潰的情況,並且這種情況可以被認為是實際的疾病或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