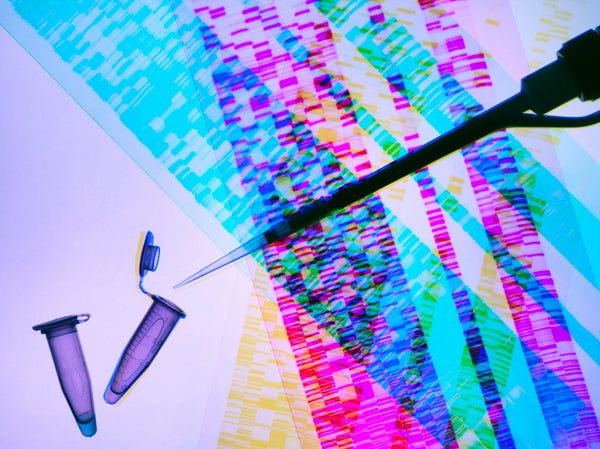在過去的20年裡,法國神經科學家厄爾萬·貝扎爾至少每兩個月會在北京待一週。貝扎爾從法國長途跋涉來到中國,是為了訪問中國實驗室裡培育的靈長類動物。
中國 已成為涉及這些動物研究的首選目的地,這些動物是研究人類疾病的寶貴模型。其他國家沒有以如此大的數量或達到中國生產的標準來培育靈長類動物。
“大約95%的使用轉基因猴子的論文來自中國,”貝扎爾說,他是 神經退行性疾病研究所 的主任,該研究所位於 波爾多大學,並且是他自己在 實驗動物科學研究所、 中國醫學科學院 的實驗室負責人。在最近的突破中, 中國科學院 (CAS) 的研究人員對食蟹猴進行了基因改造,使其表現出類似自閉症的行為,以便更好地瞭解該疾病的病因以及如何治療。中科院的科學家還使用類似於克隆多莉羊的技術克隆了靈長類動物。貝扎爾使用恆河猴展示了腦機介面如何在脊髓損傷後恢復腿部運動。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這些發展與中國生物科學領域國際標準的監管和執行的改進同時發生。兩個事件對這一過程至關重要:2003年的SARS爆發,這突顯了野生動物和實驗動物管理的問題,以及2001年中國創造了世界上首個人-兔胚胎,這引發了該國的國際公關危機。
中國政府認識到生物科學將在其全球競爭力中發揮重要作用。生物醫學、合成生物學和再生醫學技術在中國“十三五”規劃中被列為戰略領域和產業。“中國不想錯過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革命,”寧波諾丁漢大學 的創新研究學者曹聰說。
科學家們也意識到,為了獲得全球對其成就的認可,他們必須遵守國際公認的規則,清華大學 的生物醫學工程師杜亞楠說,她在哈佛-麻省理工學院健康科學與技術 工作三年後於2010年回到中國。
中國生命科學家利用先進的醫學影像技術更好地檢測肺部惡性結節,創造了首批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的猴子,並發現胎兒DNA會透過母親的血液流動。這一進展促成了妊娠期間唐氏綜合徵的無創檢測方法的開發,該方法已在世界各地使用。
在自然指數中,中國是生物醫學工程文章的第二大貢獻者,僅次於美國,這是根據其在2015-17年82種高質量研究期刊的論文作者貢獻來衡量的。
交叉審查
2001年,這樣的進步是不可想象的。在那年9月,中國報紙報道說,中山大學 在廣州的科學家陳席先成功培育出了注射了來自一名七歲男孩的皮膚細胞核的兔胚胎。
“當時,沒有人認為中國能夠取得這樣的突破,”肯特大學 的社會學家張潔說,該大學位於英國。由此產生的雜交體可以用於提取人類胚胎幹細胞,這對於再生醫學很有用。
國家的反應是樂觀的,但很短暫。幾天之內,國際社會對這項研究一片譁然,中國被稱為生物學的“狂野西部”。張潔說,政府被這場風波嚇了一跳,有效地禁止了所有雜交胚胎幹細胞研究。陳席先的雜交研究戛然而止,但他仍然留在中山大學任教,並繼續指導學生,特別是關於體細胞(非生殖)幹細胞的研究。
自那次事件以來,中國的生物倫理學格局發生了變化。2003年,科技部 和當時的衛生部(衛生部)釋出了人類胚胎幹細胞研究的指導方針。2009年至2013年間,衛生部出臺了管理醫療技術和幹細胞臨床應用的行政措施和法規。實驗室動物機構國家標準於2014年生效。
張潔將政府的監管方法描述為務實的,其中“複製貼上”了國際法規,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英國相對寬鬆的立場。張潔說,透過為研究清除監管障礙,中國吸引了許多海外華人科學家和非華裔合作者。“寬鬆的監管幫助了中國的快速崛起,”張潔說。
知情同意
2010年回到北京後,杜亞楠經歷了實驗室文化衝擊。研究人員在不同的條件下飼養實驗動物,並在沒有進行人道主義程式的情況下殺死它們。醫生在沒有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將患者樣本交給研究人員。
這些做法雖然權宜之計,但卻帶有嚴重的風險。不擇手段的行為會使科學受到批評,並可能使研究失去在頂級期刊上發表的資格。而且,未能遵守程式會破壞結果的可重複性。
提交給許多信譽良好的期刊的稿件必須附有倫理委員會的批准。自從他回國以來的幾年裡,杜亞楠——他是最近幾篇關於將幹細胞引入體內的方法的論文的合著者——目睹了生物醫學研究倫理方面的巨大進步。
例如,國際實驗動物評估和認證協會(AAALAC International)於2006年首次認可了中國的機構;到2016年,大約有60箇中國專案獲得了該組織的認證,該組織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在一個自願認證框架下促進科學中動物的負責任的護理和使用。中國也開始在全球政策辯論中採取更多主動,並在幹細胞和合成生物學等新興領域制定標準。
當2015年中國研究人員首次在非整倍體人類胚胎上使用CRISPR時,引發了另一場全球倫理辯論,張潔說,政府的反應比最近過去要剋制得多。政府澄清了其立場和監管程式,明確規定中國允許胚胎基因編輯用於基礎和臨床前研究,但禁止用於臨床或生殖用途。
廣闊的後院
但是,在倫理實踐中,中國科學仍然存在很大的差異。關於如何實施大方向指導方針的決定留給機構和研究人員自行決定。最近南方科技大學(南科大)的賀建奎聲稱基因編輯了雙胞胎,南科大已經與他劃清界限,超過100名中國生物醫學研究人員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就是一個例證。
杜亞楠說,實施仍然參差不齊,尤其是在偏遠地區的大學和醫院。他說,當談到在整個中國強制執行標準做法時,“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張潔說,部分問題在於溝通。她說,良好的執法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監控,還需要公眾參與,瞭解“他們應該期望什麼,以及他們在法律上有權得到什麼”。張潔說,未能與公眾利益團體就規則進行互動,助長了謠言、誤解和對科學的不信任的蔓延。
本文經許可轉載,並於2018年12月12日首次發表。
自然 564, S66-S68 (2018)
doi: 10.1038/d41586-018-07692-4
本文是自然指數2018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份編輯上獨立的增刊。廣告商對內容沒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