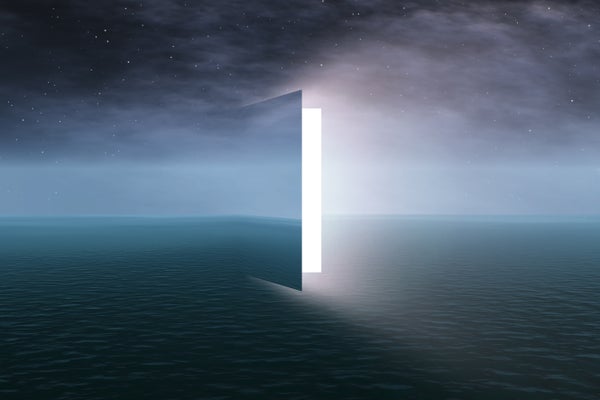在查爾斯·狄更斯備受喜愛的小說《聖誕頌歌》中,脾氣暴躁的埃比尼澤·斯克魯奇在聖誕節過去和現在的幽靈向他展示他的殘忍和自私如何傷害他人時,他仍然無動於衷。只有當未來聖誕節的幽靈以他的墓碑的形式讓斯克魯奇直面自己的無常時,這個老吝嗇鬼才開始對他人表現出仁慈和同情。
新冠病毒大流行使我們所有人都更接近自己的無常。面對臨時太平間的照片和報道死亡人數的可怕頭條新聞,我們看到,從湯姆·漢克斯到鮑里斯·約翰遜,我們所有人都很脆弱——這是一個我們在威脅較小的時期會從腦海中推開的事實。
但是,我們對這種增強的死亡感的反應可能會令人眼花繚亂地不一致。我們已經看到許多令人驚歎的人們在大流行期間挺身而出幫助他人:從一位99歲的老兵在他的花園裡走圈為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籌集了3300萬美元,到一位皇家女帽製造商開始為醫院工作人員製作面罩。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有人囤積槍支,囤積罐頭食品和衛生紙,並透過違抗科學來使他人面臨危險。
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 訂閱來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有關發現和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心理學的研究結果有助於解釋這些截然相反的反應——以及我們如何遵循我們最好的本能而不是最壞的本能。這一切似乎都歸結於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正如文化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貝克爾在1973年所暗示的那樣,我們反思自我的能力給人類帶來了問題:對自我存在的意識意味著它有一天會停止存在。在心理學中,恐懼管理理論研究當死亡對我們變得突出時,我們如何反應。在他們的書《核心之蟲》中,謝爾頓·所羅門和他的同事描述了恐懼管理理論是如何從假設開始的,即像其他生物一樣,人類具有自我保護和生存的本能。但與其它生物不同的是,我們的智力能力讓我們痛苦地意識到,我們終將死去。
反思死亡是痛苦的,但它也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國拉比約書亞·L·利布曼在他的書《心靈的平靜》中所寫的那樣,“死亡不是生命的敵人,而是它的朋友,因為正是我們對生命有限的認識才使得它如此珍貴。”有一些證據支援這一說法。在一組經歷過院外心臟驟停的患者中,那些最接近瀕死體驗的患者變得更能容忍他人的差異,更好地理解自己,更欣賞自然,並報告說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
在他告別的《紐約時報》專欄中,已故的神經學家和作家奧利弗·薩克斯寫道,在得知自己患有晚期癌症後,他並沒有結束生命。“相反,”他寫道,“我感到無比地活著,我希望並希望在剩下的時間裡加深我的友誼,向我愛的人告別,寫更多的東西,如果我有力氣就去旅行,以達到新的理解和洞察力水平。”
在一系列研究中,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勞拉·卡斯滕森和她的合著者表明,我們選擇如何度過我們寶貴的時間取決於我們認為還剩下多少時間。一旦生命的脆弱性成為一個個人的真相,而不是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哲學概念,我們就更有能力慶祝剩下的每一天和經歷,而不是專注於日常的煩惱。承認我們的無常讓我們更加關注生活中的小瞬間以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裡,您是否注意到街上人們彼此微笑的次數更多,或者他們在眼神交流和問候方面變得更自由?也許您不經常見到的人正在與您建立Zoom通話以重新取得聯絡。或者,也許您正在與親人一起開闢更有意義的日常活動,從一起做飯到定期影片聊天。在大流行期間,我們中的許多人意識到,我們的機會和人際關係正在倒計時。
人類有著利用生命的脆弱性來更好地珍惜時間的歷史。中世紀的僧侶在他們的書桌上放著一個人的頭骨,以幫助他們反思自己的無常。17世紀的繪畫流派,稱為“虛空”,具有相同的功能——例如,透過描繪一個在枯萎的花束或與人類頭骨並排的成熟水果旁滴答作響的金懷錶。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建議讓死亡進入我們的意識,以激發我們對生活更深的欣賞和幫助人類同胞的更大動力。
有些人將這種意識推向極限。亞歷克斯·霍諾爾德獨自攀登山脈的陡峭表面,例如優勝美地國家公園的埃爾卡皮坦峰——沒有繩索或支撐。“我覺得任何人都有可能在任何一天死去,”他在紀錄片《徒手攀巖》中說。“徒手攀巖讓它感覺更加直接和真實……當你沒有繩索攀爬時,後果顯然要高得多——專注程度要高得多。”
接近死亡可以讓許多人擺脫日常生活的束縛,並努力做出他們最好的貢獻。它也使一些人更加親社會——也就是說,更願意給予他人。這種效果的部分原因是,為社會做出貢獻是永遠活下去的一種方式。對死亡的頻繁提醒加強了“將自己的物質投入到能夠超越自我的生命和工作形式中的願望,”密歇根大學迪爾伯恩分校的退休心理學教授約翰·科特在1984年的一本書中寫道。
在一項名為“斯克魯奇效應”的系列研究中,當時在德國路德維希馬克西米利安大學的研究員伊娃·喬納斯和她的同事發現,當人們在殯儀館前接受採訪時,他們對慈善機構更為有利——例如,他們認為某個慈善機構對社會更有益——而不是在幾個街區之外接受採訪。當美國參與者有機會向一家美國慈善機構捐款時,那些被要求寫下自己死亡的人的捐款比那些被要求寫牙痛的人高出約400%。
有趣的是,然而,同一研究中的參與者並沒有向一家外國慈善機構捐出更高的捐款,因為那會使與他們不同的人受益。正如這一發現所表明的那樣,當死亡突出時(就像現在的新冠病毒一樣),我們可以走向任何一個方向:我們可能會受到激勵做出積極的改變,但我們也可能更容易陷入陷阱,陷入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群體偏見。
例如,在一項研究中,當時都在亞利桑那大學的亞伯蘭·羅森布拉特和傑夫·格林伯格讓真正的法官閱讀了一名被指控從事賣淫行為的女性的假設檢察官筆記。在要求法官設定她的保釋金之前,研究人員讓他們填寫了一份性格問卷。一些法官收到了一個問題,要求他們簡要描述當他們想到自己的死亡時的情緒。“我想我會為我的家人感到非常難過,他們會想念我,”一個典型的回答寫道。
其他法官沒有得到任何以死亡為導向的問題。他們將保釋金定為 50 美元——這是該犯罪的平均水平。那些被引導思考自己道德的人更加嚴厲:他們設定的平均保釋金為 455 美元,是控制組法官的九倍之多。研究結束後,法官們堅持認為回答有關他們死亡的問題不可能影響他們的法律決定。畢竟,他們的工作是成為根據事實衡量案件的理性專家。但證據表明並非如此。
為什麼當人們思考死亡時,有時會變得思想封閉和道貌岸然,而不是專注於幫助他人?因為我們的道德、群體和國家將在我們之後繼續存在。如果我們不小心,對死亡的焦慮會讓我們執著於當地的文化,這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延續生命”。因此,被鼓勵反思死亡的法官不僅想給那個女人一記耳光,還想給她“應得”的懲罰,因為她違反了道德。如果讓死亡意識讓你感到焦慮而不是反思,你就會試圖透過道德說教、民族主義、攻擊其他文化甚至支援戰爭來積極地保護你的世界觀。
這是死亡意識的另一面:當我們的反應從反思轉向焦慮時,我們的行為變得更加自我保護。我們成為自私偏見的犧牲品,多元化努力困擾著我們——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亞當·格蘭特和杜克大學教授金伯利·韋德·本佐尼描述了這種影響。這就是為什麼提出戰爭威脅的民族主義政客會贏得支持者來阻止外國人:思考我們可能的死亡會把我們變成自以為是、好鬥、目光短淺的仇外者。
我們都有權選擇如何應對我們在大流行期間正在經歷的死亡意識。當我們能夠反思死亡而不屈服於對其的焦慮時,我們可能會做出選擇,幫助我們做出最好的貢獻並改善世界,而不是退縮或猛烈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