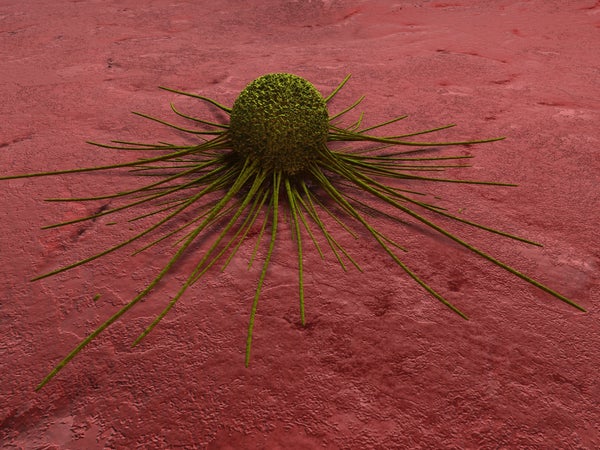大約六年前,阿爾貝託·巴爾德利陷入了科學上的低谷。作為義大利都靈大學的癌症生物學家,他一直在研究靶向療法——針對驅動腫瘤生長的突變而定製的藥物。這種策略似乎很有前景,一些患者開始出現令人矚目的康復。但是,腫瘤不可避免地會對藥物產生抗藥性。巴爾德利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他們復發。“我撞上了一堵牆,”他說。巴爾德利意識到,問題不在於特定的突變,而在於進化本身。“不幸的是,我們正面臨著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力量之一,”他說。
研究人員長期以來一直理解腫瘤會進化。隨著腫瘤的生長,突變產生,並出現基因不同的細胞群。對治療產生抗藥性的細胞存活並擴張。無論醫生使用什麼藥物,腫瘤似乎都會適應。研究人員一直難以解析這個過程,因為癌症在體內進化需要數年時間。“我們過去常常對患者說,癌症是以達爾文主義的方式進化的,但我們沒有大量的證據來真正正式地證明這一點,”倫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癌症研究員查爾斯·斯旺頓說。
這種情況正在開始改變。由於測序技術的進步以及大量樣本和臨床資料的收集,科學家們正在拼湊出癌症如何進化的更精確圖景,揭示耐藥性的根源,並在某些情況下,找出如何克服耐藥性。隨著治療手段的不斷增加,生物學家們正試圖利用這些見解。
支援科學新聞事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事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癌症在不斷適應,因此我們也必須這樣做,”巴爾德利說。本著這種精神,去年他將實驗室的重點轉向研究癌症的進化。他的團隊已經模擬了結直腸癌如何對組合使用的靶向療法作出反應,可能揭示了防止腫瘤細胞產生耐藥性的方法。“我們現在有非常令人興奮的資料,關於追蹤和治療進化的可能性,”他說。
生命之樹
癌細胞蘊藏著驚人數量的突變。2012年,當斯旺頓和他的同事對兩名腎癌患者的多個活組織樣本進行測序時,他們發現即使在同一個人體內,也沒有兩個樣本是相同的。該團隊不僅檢查了原發腫瘤,還檢查了衛星腫瘤——稱為轉移瘤——這些腫瘤已經擴散到患者全身。在每個人體內,該團隊在分析的各種腫瘤樣本中發現了100多個突變;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突變發生在所有樣本中。
來自同一個人的各種癌細胞之間的關係可以像進化生物學家繪製物種之間的關係一樣繪製出來:透過繪製系統發育樹,分支圖追溯“後代”到共同祖先。發生在第一個惡性細胞中的突變,即進化樹樹幹中的突變,將最終出現在所有腫瘤細胞中;稍後出現的突變將僅在樹的分支中發現。斯旺頓說,要消除腫瘤,必須攻擊樹幹中的突變。

尼克·斯賓塞/《自然》
《自然》新聞,2016年4月13日,doi:10.1038/532166a
針對其中一些樹幹突變的療法已經存在,它們通常在最初產生顯著的效果。但是,正如巴爾德利發現的那樣,隨後會產生耐藥性。“我們如此專注於‘腫瘤越小越好’,但人們沒有想到的是留下了什麼,”斯旺頓說。“你經常留下無法治療的耐藥克隆。”但他認為,透過同時靶向多個樹幹突變,研究人員可能有機會消滅癌症。單個癌細胞能夠逃避兩管齊下或三管齊下的攻擊的可能性很小。
一種方法是使用靶向療法的組合。“理論上,它們可以奏效,”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西德尼·金梅爾綜合癌症中心的癌症遺傳學家伯特·沃格爾斯坦說。事實上,當他和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的進化生物學家馬丁·諾瓦克對該策略進行建模時,他們發現兩種沒有共同耐藥機制的靶向藥物足以控制轉移性癌症。對於有大量轉移瘤的人,該模型表明需要三種療法。
研究人員已經開始在臨床上測試靶向療法的組合。然而,斯旺頓指出,絕大多數突變都沒有靶向藥物。而且,以不損害患者的方式組合現有藥物已被證明是棘手的。因此,斯旺頓專注於免疫療法——幫助免疫系統識別和摧毀癌細胞的策略。
免疫系統識別威脅,部分是透過檢測細胞表面,尋找稱為抗原的分子,這些分子可以發出內部問題的訊號。癌細胞DNA中的基因缺陷有時可以編碼抗原,從而引發免疫反應。但是,斯旺頓和他的同事想知道,免疫系統對抗原的反應是來自癌症的進化樹幹還是來自其分支,這是否重要。
在三月份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他和他的同事檢查了來自癌症基因組圖譜的樣本,該圖譜收集了數千名癌症患者的遺傳和臨床資料。他們發現,患有肺癌的人,如果有很多樹幹抗原——以及樹幹抗原與分支抗原的比例較高——比那些樹幹抗原少或分支抗原比例較高的人活得更久。更重要的是,樹幹抗原多的人似乎對免疫療法的反應更好。斯旺頓說,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如果免疫系統靶向樹幹抗原,它就會擊中大多數癌細胞,而不是“掐掉小樹枝”。
這項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但斯旺頓正在領導一項臨床研究,這可能有助於證實他的發現。這項名為TRACERx——透過治療(Rx)追蹤癌症進化的研究,將跟蹤850名肺癌患者從確診到治療,在某些情況下,直到死亡。它將記錄他們腫瘤的基因變化,以檢查肺癌如何進化,以及治療如何影響這個過程。
一旦獲得資料,斯旺頓希望籌集足夠的資金來測試基於進化的治療策略。一種方法是識別腫瘤中的免疫細胞,在實驗室中培養它們,然後將它們輸回患者體內——這種技術稱為過繼細胞轉移。目前使用的類似策略選擇識別任何癌症抗原的免疫細胞,但斯旺頓的團隊將選擇那些準備識別所有癌細胞上都存在的樹幹抗原的免疫細胞。
這種策略並不便宜,但一連串的靶向療法最終都失敗了,代價也不菲。“每個療程的費用在1萬美元到10萬美元之間,”斯旺頓說。如果研究人員能夠開發出一種可以治癒轉移性癌症的療法,“整個成本效益分析和衛生經濟模型都會發生巨大變化”。
細胞競爭者
應用進化原理可能有助於免疫系統戰勝腫瘤。佛羅里達州坦帕市莫菲特癌症中心的分子腫瘤學家羅伯特·加滕比有一個更適度的目標:他希望幫助人們與疾病共存。加滕比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從進化的角度思考癌症問題,當時他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工作。他看到太多人復發,以至於癌症開始看起來不像是一個生物學問題,而更像是巫術。“這就像一個邪惡的實體,不斷地復發並戰勝你最好的努力。”但當他開始從進化的角度思考癌症時,問題再次變得容易處理,他說。
加滕比開始嘗試對該疾病進行數學建模,以找出最佳的治療方法。他的模型表明,許多腫瘤學家正在採取錯誤的方法。通常,醫生會給予患者可以耐受的最大劑量的化療,以儘可能多地殺死癌細胞。希望他們能在耐藥性進化之前消滅癌症。
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腫瘤在遇到治療之前很久就存在耐藥細胞。耐藥細胞群保持較小規模,因為耐藥性會帶來適應性成本。然而,當患者接受大劑量化療時,耐藥細胞變得比敏感細胞更適應。加滕比將耐藥性比作雨傘:“如果下雨,雨傘非常有用。但如果不下雨,它就是一種負擔。”加滕比認為,他可以透過更仔細地管理藥物劑量或時間來利用敏感細胞和耐藥細胞之間的自然競爭。
最近,他在患有兩種乳腺癌的小鼠身上測試了這個想法。當他和他的同事給小鼠注射標準的、最大耐受劑量的化療藥物紫杉醇時,一旦停止治療,腫瘤就會迅速反彈。該團隊還嘗試在腫瘤開始縮小後跳過劑量,但這並沒有更好的效果。第三組小鼠最初接受了標準的高劑量化療,但一旦動物的腫瘤開始縮小,研究人員就調低了劑量。這種策略使小鼠的存活率最高,並使五隻受試小鼠中的三隻完全停止用藥。這種治療旨在適應腫瘤的反應,並在耐藥細胞和敏感細胞之間保持平衡(參見“進化的策略”)。“我認為這是癌症生物學中最令人興奮的進展之一,因為它是一個相對容易嘗試的事情,”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坦佩分校的生物學家卡洛·馬利說,他曾與加滕比合作。
2015年5月,莫菲特癌症中心啟動了一項試點研究,以測試這種適應性療法是否有助於前列腺癌患者。醫生將監測患者的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水平,這是疾病進展的標誌。然後,他們將根據所看到的情況,進行標準治療或停止治療。研究人員過去曾研究過間歇性治療,但方案通常涉及嚴格控制的週期。“使用適應性療法,開-關週期由腫瘤反應決定,”加滕比說。他還計劃使用來自試驗的大量分子和臨床資料來開發計算機模型,這些模型可能在未來指導適應性療法。
進退兩難
醫生們已經注意到其他進化範例在起作用。今年一月,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的胸腔腫瘤學家傑弗裡·恩格爾曼和他的同事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詳細介紹了波士頓一名52歲轉移性肺癌婦女的病例。該婦女的腫瘤有一種基因重排,產生了畸形的ALK蛋白,因此她的醫生首先給她服用了克唑替尼,這種藥物可以抑制ALK的作用。她在18個月內反應良好,但隨後復發。第二代療法也失敗了,因此醫生轉而使用仍在臨床試驗中的第三代療法。這種療法起作用了一段時間,但不到一年後,該婦女的肝臟開始衰竭,她不得不住院治療。然後她的醫生髮現,第三代療法促使產生了一種新的突變,使她的癌症再次對克唑替尼產生反應。當他們給她服用這種藥物時,她的肝臟恢復了,她的病情好轉了很多,以至於能夠出院。
對於恩格爾曼和他的同事來說,該婦女對克唑替尼的再敏感化是一個意外的驚喜。但研究人員或許能夠有意地引導癌症走上這樣的道路。加滕比稱這種策略為進化雙重束縛,他這樣解釋它:想象一下,試圖透過引入捕食者(如鷹)來控制鼠群,鷹可以從空中將它們抓走。這種型別的捕食選擇了躲在灌木叢下的齧齒動物。因此,人們可能會引入也躲在灌木叢下的蛇。蛇會選擇喜歡開闊空間的鼠,使它們容易受到鷹的攻擊,加滕比說。同樣的想法也可能適用於癌症。使用一種治療方法,使癌症更容易受到第二種治療方法的影響,然後在兩者之間交替進行。加滕比說,這“不是打地鼠”,而是“一種經過仔細思考的方法,它利用了進化動力學”。
澳大利亞墨爾本彼得·麥卡勒姆癌症中心的癌症研究員本·所羅門計劃在即將到來的試驗中測試這種策略。許多肺癌患者攜帶一種名為EGFR的基因突變。幾種藥物已被批准用於靶向EGFR突變,但腫瘤總是會對這些藥物產生耐藥性。在約一半的患者中,這種耐藥性是由EGFR中稱為T790M的突變引起的。去年,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了一種名為奧希替尼的靶向藥物,它可以抑制標準的EGFR突變以及T790M,但對該藥物有反應的人往往會在一年內復發。
所羅門和他的同事計劃首先讓試驗參與者服用奧希替尼,然後透過追蹤血液中迴圈的腫瘤DNA來監測耐藥性。研究人員預計會看到T790M突變減少。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他們將轉而使用不抑制T790M的第一代EGFR抑制劑。當T790M水平升高時,研究人員將切換回奧希替尼。“我們的假設是,這將延遲奧希替尼耐藥性的出現,因為我們沒有維持這種選擇壓力,”所羅門說。他希望很快獲得該試驗的最終批准。
不能保證這些策略中的任何一種都會奏效。但即使試驗失敗,測試結果也將幫助研究人員改進他們的理論,並將解決一些大的未知數。例如,腫瘤中基因不同的細胞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它們所處的細胞環境又起什麼作用?哈佛醫學院的腫瘤學家科妮莉亞·波利亞克說,癌症研究人員傾向於關注細胞內部的突變,而忽略了這些突變細胞可能如何影響周圍的細胞。“這是一個很大程度上未被探索的領域,”她說。
腫瘤內部的動力學非常複雜,但恩格爾曼並沒有氣餒。臨床分析將幫助研究人員理解這種複雜性。“這些見解將使我們更接近於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他說。“令人沮喪的是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本文經許可轉載,並於2016年4月13日首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