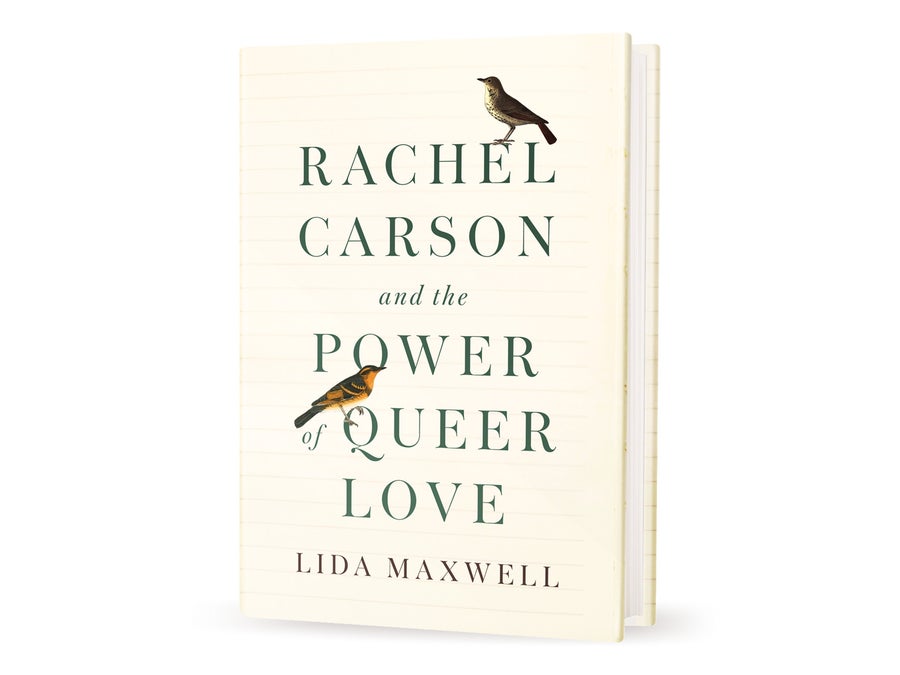非小說
蕾切爾·卡森與酷兒之愛的力量
作者:莉達·麥克斯韋爾。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25年(25美元)
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夜,兩位女性並肩躺在狗魚頭,那是緬因州鋸齒狀海岸上的一片狹長土地,河流在此匯入海洋。她們欣賞著耀眼的星空、模糊的銀河絲線,以及偶爾劃過的流星。其中一位女性是蕾切爾·卡森,她後來因其著作《寂靜的春天》及其對現代環境運動的推動而聞名;另一位是多蘿西·弗里曼,卡森已婚的鄰居。兩人自1953年在緬因州南波特島相遇的那一刻起就被彼此吸引,並保持親密關係直至1964年卡森因癌症去世。是弗里曼撒了卡森的骨灰。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狗魚頭的場景聽起來可能很浪漫,莉達·麥克斯韋爾的新書《蕾切爾·卡森與酷兒之愛的力量》認為它確實如此。麥克斯韋爾是波士頓大學政治學以及女性、性別和性研究教授,她部分透過大量私人信件,探討了卡森和弗里曼之間的親密關係。這本書的資訊是,這種關係為我們當今的氣候危機提供了一個教訓,特別是對於那些願意在我們文化的主流敘事之外尋找意義的人來說。
這些信件很有說服力。卡森在僅僅幾封信後就表達了強烈的感情(“因為我愛你!現在我可以繼續告訴你我愛你的原因,但這需要很長時間,而且我認為簡單的事實涵蓋了一切……”)。兩人互稱“親愛的”和“甜心”。在她們身體分離的時期,她們表達了可以很容易被解讀為酷兒渴望的情感,例如弗里曼寫道:“我多麼想蜷縮在你身邊,坐在書房的沙發上,對著爐火凝視,沒完沒了地聊天。”
還有提到我們永遠無法讀到的數百封信件,因為兩位女性燒燬了它們,也許就在那個壁爐裡。正如多蘿西的孫女瑪莎·弗里曼告訴麥克斯韋爾的那樣,“蕾切爾和多蘿西最初對她們通訊中浪漫的語氣和術語持謹慎態度。”
卡森是女同性戀嗎?長期以來,答案一直是猜測的來源。這不可能知道;眾所周知,她沒有公開承認自己是女同性戀。然而,對麥克斯韋爾來說,這個問題無關緊要:“無論她們的愛是否是‘同性戀’,用當時的語言來說,它肯定是酷兒的。它將她們從傳統的婚姻和家庭形式中拉出來,讓她們在社會告訴她們不應該找到幸福的地方找到了幸福:在彼此相愛和非人類自然世界中。”
酷兒之愛是對麥克斯韋爾所說的“異性戀之愛的意識形態”的拒絕,或者透過婚姻、購買和裝飾房屋、生育和撫養子女以及參與消費文化的跑步機來維持一切運轉來追求“美好生活”。麥克斯韋爾認為,由於卡森和弗里曼的愛是酷兒的,她們沒有可以探索它的模板。相反,她們創造了一種新的語言,透過對自然共同的熱愛來表達:知更鳥的歌聲、緬因州的潮汐池、她們房子之間的樹林。麥克斯韋爾認為,這種聯絡和意義創造的途徑,使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成為可能——它將她從一位捕捉自然奇觀的作家轉變為一位倡導拯救自然的作家。
這如何應用於氣候危機?麥克斯韋爾寫道:“也許顯而易見的是,異性戀之愛的意識形態與消費的緊密聯絡對我們的氣候也是不利的,因為它將我們親密的幸福與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聯絡起來。”她繼續說,為了真正實現有意義的氣候政策,我們需要擴充套件我們“對美好生活可能是什麼樣子的發自內心的想象”。酷兒版本擁抱“充滿活力的多物種世界”,我們在其中尋求“資本主義和異性戀之愛意識形態之外的慾望和快樂”。貫穿全書的這些具體觀點有時是重複的,並且可能讓人感到說教。
一些讀者,特別是異性戀讀者,可能會對這一切感到惱火。畢竟,很多不認為自己是酷兒的人也選擇退出消費主義並與氣候變化作鬥爭。異性戀者可以拒絕異性戀規範的故事;酷兒群體也並非對此免疫。但這本書的重點不是我們應該採取個人行動——而是關於更廣泛的結構和敘事。作為一個在異性戀規範婚姻中度過了十年的酷兒女性,我知道那種特定的“美好生活”的召喚有多麼誘人;我也知道建立新事物的解放。麥克斯韋爾的書對所有讀者都有關於承認,然後逃脫束縛我們的結構的教訓。
卡森和弗里曼透過她們明確的酷兒、深刻浪漫、持久的愛找到了出路。即使在她們分開時,她們也想象著彼此在一起。正如弗里曼在其中一個時期寫道:“你和我一直在月光下在海岬上散步。你還記得我們在那美好的光線下躺在那裡的那個夜晚嗎?我告訴你你看起來像雪花石膏。你確實是。那時我們多麼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