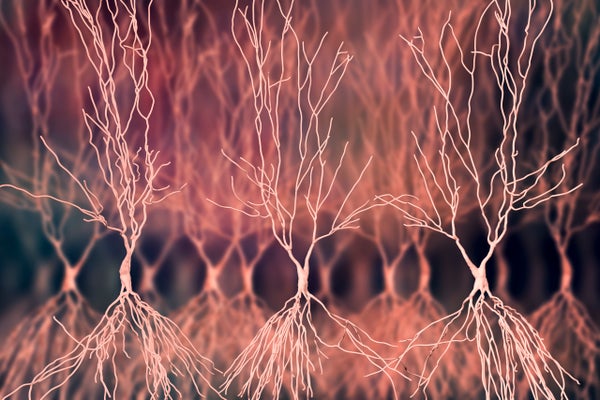特定的大腦活動模式被認為是大腦特定過程或計算的基礎,這些過程或計算對於各種心理功能(如記憶)至關重要。最近備受關注的一種“大腦訊號”被稱為“尖波紋波”——一種短促的、波形的高頻振盪爆發。
研究人員最初在海馬體中發現了紋波,海馬體是大腦中至關重要的記憶和導航區域,認為紋波對於在睡眠期間將記憶轉移到長期記憶中至關重要。然後,2012年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科學家洛倫·弗蘭克和尚塔努·賈達夫(後者現就職於布蘭迪斯大學)領導的一項研究表明,紋波在清醒時的記憶中也發揮作用。研究人員使用電脈衝干擾齧齒動物大腦中的紋波,並表明,透過這樣做,記憶任務的表現會降低。然而,沒有人操縱紋波來增強記憶——直到現在。
紐約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在神經科學家格爾吉·布扎基的領導下,現在正是這樣做了。在6月14日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一項研究中,該團隊表明,延長大鼠海馬體中的尖波紋波顯著提高了它們在迷宮任務中的表現,該任務考驗工作記憶——大腦用於即時組合和處理資訊的“草稿紙”。“這是一項非常新穎且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未參與該研究的賈達夫說。“以如此精確的方式對生理過程進行‘功能獲得’研究非常困難。”這項工作不僅揭示了關於紋波如何促進特定記憶過程的新細節,而且最終可能對開發記憶和學習障礙的干預措施產生影響。
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研究人員首先檢查了多年實驗中獲得的資料庫中記錄的大鼠在執行任務時紋波的特性。他們發現,當大鼠必須穿過迷宮時,比簡單地探索或沿著軌道奔跑時,會發生持續時間更長的紋波。穿過迷宮需要大鼠運用記憶力。
在一項名為 M 迷宮的任務中,大鼠首先被訓練成穿過 M 形迷宮的右臂以獲得含糖獎勵,然後在下一次試驗中穿過左臂。研究人員發現,與做錯的試驗相比,大鼠正確完成的試驗中紋波持續時間明顯更長。“你可以記錄大腦中非常簡單的電模式,並判斷動物的表現是好還是不好,或者動物是否在學習,”布扎基說。這些發現表明,海馬體在記憶密集型活動期間會產生持續時間更長的紋波,並且這些持續時間更長的訊號可以提高表現。
為了驗證持續時間更長的紋波有助於提高表現,研究小組人為地延長了執行 M 迷宮任務的大鼠的紋波持續時間。研究人員使用了光遺傳學,即使用光纖電纜輸送的光來啟用大鼠海馬體中基因工程改造的光敏神經元。他們記錄了任務期間海馬體中的集體神經活動,以便他們能夠檢測到自發產生的紋波。一旦檢測到紋波,就會觸發光脈衝來啟用工程改造的神經元。與沒有光刺激或在短暫的隨機延遲後施加刺激的對照條件相比,這種“閉環”刺激使紋波的持續時間大約增加了一倍,並顯著提高了大鼠的表現。
大鼠的學習速度也更快,在記住哪條路線會帶來獎勵方面,達到 80% 的正確率的時間早於對照條件下的老鼠。研究人員還透過使用高強度光脈衝中止紋波來關閉任何有益效果,證實了表現受到損害。“很高興看到另一個小組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做了一些事情,並獲得了相同的結果,”弗蘭克說。“這讓你感覺我們都在朝著某個方向前進。”
為了研究更長的紋波可能如何提高表現,研究小組檢查了參與神經元的特性。紋波不僅僅是相同神經元隨時間推移的重複活動;相反,隨著訊號的持續,其活動會擴散到更多神經元。
研究小組觀察到,特定的神經元傾向於在訊號的早期或晚期“放電”,並且他們發現了這兩組神經元之間有趣的差異。“早期”神經元是具有高基線活動的“話匣子”,而“晚期”神經元則更加遲緩,平均活動較低。“放電快的神經元就像健談的人,他們在許多情況下都很活躍,”布扎基解釋說。“大多數神經元通常不放電,但一旦放電,它們就會說出重要的事情。”
海馬體包含專門用於導航的神經元,稱為“位置細胞”,當動物處於特定位置時,這些細胞會放電。研究人員發現,在長紋波的後期(無論是自發產生的還是人為延長的)放電的神經元,對位置的調諧度更高,並且這些位置往往位於迷宮的臂上。之前的研究表明,紋波的一個功能可能是“重放”記憶。新的發現支援了這一觀點,並表明延長紋波會招募額外的神經元來生成訊號,這些神經元的活動與手頭的任務相關。“當他們延長紋波的長度時,他們正在招募重新啟用動物採取的路徑的細胞,”賈達夫解釋說。“這可能是一種對所有可用路徑進行認知搜尋的機制,其他大腦區域可以讀取並採取行動。”
研究人員希望這項工作最終可能有助於開發治療與年齡相關的認知衰退或阿爾茨海默病中出現的記憶問題的方法。學習困難也可能得到解決。實驗中的技術很難應用於人類,因為它們具有侵入性並且涉及基因操作,但布扎基表示他們正在研究非侵入性方法。最近一項研究於 4 月份發表,由波士頓大學神經科學家羅伯特·萊因哈特領導,該研究使用應用於老年參與者頭皮的微弱電流來提高工作記憶表現,同時伴隨著不同皮質區域中某些(theta)頻率的振盪之間更大的同步性。“[布扎基團隊]的優雅工作與我的實驗室進行的研究之間存在有趣的聯絡點,”萊因哈特說。“系統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正在奠定關鍵的基礎科學基礎,這可能會為預防和治療腦部疾病開闢全新的基於迴路的療法途徑。”
現有非侵入性方法(如經顱磁刺激或萊因哈特研究中使用的經顱電刺激技術)的問題在於它們無法穿透大腦,因此難以操縱深層海馬體中的訊號。非侵入性地從大腦深處記錄更加棘手。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從大腦表面記錄的活動中推斷海馬體中何時發生紋波。“可能存在非常特定的、比如說,先於這些事件併產生海馬體紋波的前額葉活動模式,”弗蘭克說。“但我們還不瞭解它的樣子。”
此外,使用這些技術修改皮質活動可能會因此影響海馬體中的活動。“我們知道這些尖波紋波可能會受到[特定的]新皮質模式的影響,”布扎基說。“事實上,許多公司都在試圖透過改變新皮質模式來影響記憶。”最後,可以採用侵入性方法,類似於用於檢測和干預癲癇發作的植入物,用於檢測或操縱紋波,或兩者兼而有之。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方法甚至可以結合使用。“只要你能測量這些事件並想出某種方法來操縱它們,你就有可能使系統執行得更好,”弗蘭克說。“那裡存在著無限的可能性。”
注意:格爾吉·布扎基的單位已從“紐約大學”更正為“紐約大學醫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