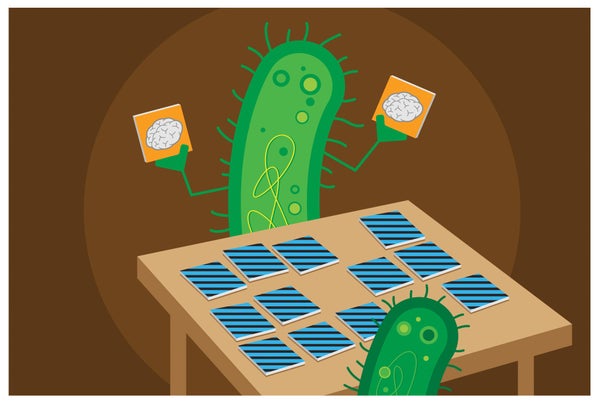即使是沒有大腦的生物也能記住它們的過去:科學家發現大腸桿菌細菌形成了它們自己對營養物質暴露的記憶。研究團隊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報告說,它們將這些記憶傳遞給後代,這可以幫助它們躲避抗生素。
達特茅斯學院微生物學家喬治·奧圖爾研究細菌結構生物膜,他說:“我們通常認為微生物是單細胞生物,每個細胞都做自己的事情。” 但實際上,細菌經常透過協同工作來生存。就像蜜蜂遷移蜂巢一樣,尋找永久家園的細菌菌落通常會以稱為群體的集體單位形式移動。
這些群體由於其高細胞密度,可以更好地抵抗抗生素暴露,這使得它們對微生物學家,如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蘇維克·巴塔查里亞特別感興趣。當他觀察到他稱之為“奇怪的菌落模式”時,他正在研究大腸桿菌的群集行為,這是他以前從未見過的。透過分離單個細菌,他和他的同事發現,細胞的行為因其過去的經驗而異。先前群集過的菌落中的細菌細胞比未群集過的細菌細胞更傾向於再次群集,並且它們的後代也至少持續了四代——大約兩個小時。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未來能夠繼續講述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有影響力的故事。
透過調整大腸桿菌基因組,科學家們發現,這種能力的基礎是兩個基因,它們共同控制鐵的攝取和調節。這種重要的細菌營養素水平低的細胞似乎容易形成移動群體。巴塔查里亞說,研究人員懷疑這些群體隨後可能會尋找具有理想鐵水平的新位置。
奧圖爾說,過去的研究表明,一些細菌可以記住並傳遞給後代關於其物理環境的細節,例如穩定表面的存在,但這項研究表明,細菌也可以記住營養物質的存在。一些細菌每小時繁殖多次,它們使用這些細節來確定一個位置的長期適用性,甚至可能一起定居在更持久的生物膜中。
奧圖爾說,除了大腸桿菌以外的微生物可能也記得鐵暴露。“如果[這些結果]在其他細菌中也站不住腳,我會感到非常震驚。” 他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在細胞水平上檢查細菌如何將鐵檢測轉化為不同的行為。
由於細菌在形成更大的結構時更難殺死,因此瞭解它們這樣做的原因最終可能會為解決頑固感染提供新的方法。奧圖爾說,這項研究為開發新的抗感染治療方法提供了機會——尤其是在抗生素在殺死這些微生物方面變得越來越無效的情況下,這一點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