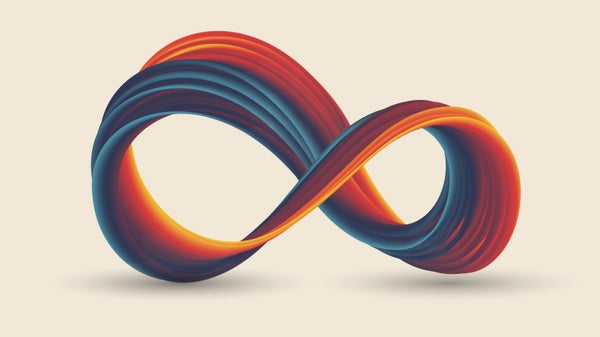諸如計數之類的簡單數學概念似乎牢固地紮根於自然的思維過程中。研究表明,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兒童和動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具備這種技能。這不足為奇,因為就進化而言,計數非常有用。例如,即使是非常簡單的貿易形式也需要計數。計數還有助於估計敵對群體的大小,從而判斷是進攻還是撤退更明智。
在過去的幾千年裡,人類發展出了一種非凡的計數概念。最初應用於少數物體,後來很容易擴充套件到極其不同的數量級。很快,一個數學框架就出現了,它可以用來描述巨大的數量,例如星系之間的距離或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數量,以及微觀世界中難以想象的距離,例如原子或夸克之間的距離。
我們甚至可以使用超出目前已知與描述宇宙相關的數字。例如,數字 1010100(1 後面跟著 10100 個零,其中 10100 表示 1 後面跟著 100 個零)可以寫下來並用於各種計算。然而,用普通的十進位制記數法寫下這個數字,將需要比宇宙中可能包含的基本粒子更多的粒子,即使每個數字只用一個粒子。物理學家估計,我們的宇宙包含少於 10100 個粒子。
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將有助於確保未來能夠繼續釋出關於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思想的具有影響力的報道。
然而,即使是如此難以想象的巨大數字,與無限集合相比也顯得微不足道,無限集合在數學中已經扮演了 100 多年的重要角色。簡單地計數物體會產生自然數集合,ℕ = {0, 1, 2, 3, …},我們中的許多人在學校都遇到過。然而,即使是這個看似簡單的概念也提出了一個挑戰:沒有最大的自然數。如果你一直數下去,你總能找到一個更大的數字。
無限集合真的存在嗎?在 19 世紀,這個問題非常有爭議。在哲學上,情況可能仍然如此。但在現代數學中,無限集合的存在被簡單地假定為真——作為不需要證明的公理被假設。
集合論不僅僅是描述集合。正如在算術中,你學習將算術運算應用於數字——例如,加法或乘法——你也可以定義集合論運算,從給定的集合生成新的集合。你可以取並集——{1, 2} 和 {2, 3, 4} 變成 {1, 2, 3, 4}——或交集——{1, 2} 和 {2, 3, 4} 變成 {2}。更令人興奮的是,你可以形成冪集——一個集合的所有子集的族。
比較集合的大小
對於小的集合 X,可以很容易地計算出集合 X 的冪集 P(X)。例如,{1, 2} 給出 P({1,2}) = {{}, {1}, {2}, {1, 2}}。但是對於較大的 X,P(X) 增長迅速。例如,每個 10 元素集合都有 210 = 1,024 個子集。如果你真的想挑戰你的想象力,請嘗試形成無限集合的冪集。例如,自然數集合 P(ℕ) 的冪集包含空集、ℕ 本身、所有偶數的集合、質數、數字之和為 2021 的所有數字的集合、{12, 17},以及更多更多。事實證明,這個冪集的元素數量超過了自然數集合中的元素數量。
要理解這意味著什麼,你首先必須理解集合大小是如何定義的。對於有限的情況,你可以計數各自的元素。例如,{1, 2, 3} 和 {康托爾, 哥德爾, 科恩} 的大小相同。如果你想比較元素眾多(但數量有限)的集合,有兩種公認的方法。一種可能性是計數每個集合中包含的物件並比較數字。然而,有時,將一個集合的元素與另一個集合的元素匹配更容易。那麼,當且僅當一個集合的每個元素都可以與另一個集合的一個元素唯一配對時(在我們的例子中:1 → 康托爾,2 → 哥德爾,3 → 科恩),兩個集合的大小才相同。
這種配對方法也適用於無限集合。在這裡,不是先計數然後再推匯出諸如“大於”或“等於”之類的概念,而是遵循相反的策略。你首先定義兩個集合 A 和 B 大小相同的含義——即,存在一個對映,將 A 的每個元素與 B 的恰好一個元素配對(因此 B 中沒有元素被遺漏)。這種對映稱為雙射。
類似地,如果存在從 A 到 B 的對映,該對映最多使用 B 的每個元素一次,則定義 A 小於或等於 B。
在我們有了這些概念之後,集合的大小用基數或勢來表示。對於有限集合,這些是通常的自然數。但對於無限集合,它們是抽象的數量,只是捕捉了“大小”的概念。例如,“可數”是自然數的基數(因此也是每個與自然數大小相同的集合的基數)。事實證明,存在不同的基數。也就是說,存在無限集合 A 和 B,它們之間沒有雙射。
乍一看,這種大小的定義似乎會導致矛盾,波西米亞數學家伯納德·波爾查諾在 1851 年 posthumously 出版的《無限的悖論》中詳細闡述了這些矛盾。例如,歐幾里得的“整體大於部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這意味著如果集合 A 是 B 的真子集(即,A 的每個元素都在 B 中,但 B 包含額外的元素),那麼 A 必須小於 B。然而,這個斷言對於無限集合是不成立的!這種奇怪的性質是一些學者在 100 多年前拒絕無限集合概念的原因之一。
例如,偶數集合 E = {0, 2, 4, 6, …} 是自然數 ℕ = {0, 1, 2, …} 的真子集。直觀地,你可能會認為集合 E 的大小是 ℕ 的一半。但事實上,根據我們的定義,這兩個集合的大小相同,因為 E 中的每個數字 n 都可以分配給 ℕ 中的恰好一個數字(0 → 0, 2 → 1, 4 → 2, …, n → n/2, …)。
因此,集合的“大小”概念可能會被駁斥為無意義的。或者,它可以被稱為其他東西:例如,基數。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將堅持傳統的術語,即使它在無窮遠處有出乎意料的後果。
在 1800 年代後期,現代集合論的創始人,德國邏輯學家格奧爾格·康托爾發現,並非所有無限集合都是相等的。根據他的證明,一個集合 X(有限或無限)的冪集 P(X) 總是大於 X 本身。除其他外,由此得出,沒有最大的無窮大,因此也沒有“所有集合的集合”。
一個未解決的假設
然而,存在類似於最小無窮大的東西:所有無限集合都大於或等於自然數。與 ℕ 大小相同的集合 X(在 ℕ 和 X 之間存在雙射)稱為可數集;它們的基數表示為 ℵ0,或 aleph null。對於每個無限基數 ℵa,都存在下一個更大的基數 ℵa+1。因此,最小的無限基數 ℵ0 之後是 ℵ1,然後是 ℵ2 等等。實數集合 ℝ(也稱為實數軸)與 ℕ 的冪集一樣大,這個基數表示為 2ℵ0,或“連續統”。
在 1870 年代,康托爾思考 ℝ 的大小是否是 ℵ0 之上的最小可能基數——換句話說,是否 ℵ1 = 2ℵ0。此前,研究過的 ℝ 的每個無限子集都被證明要麼與 ℕ 一樣大,要麼與 ℝ 本身一樣大。這導致康托爾提出了所謂的連續統假設 (CH):斷言 ℝ 的大小是最小的不可數基數。幾十年來,CH 讓數學家們忙碌不已,但他們一直無法證明。後來,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他們的努力從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
集合論非常強大。它可以描述幾乎所有的數學概念。但它也有侷限性。該領域基於 100 多年前由德國邏輯學家恩斯特·策梅洛提出的,並由他的德裔以色列同事亞伯拉罕·弗蘭克爾詳細闡述的公理系統。這個系統被稱為 ZFC,或策梅洛-弗蘭克爾集合論(C 代表“選擇公理”),是一組基本假設,足以執行幾乎所有的數學運算。極少有問題需要額外的假設。但在 1931 年,奧地利數學家庫爾特·哥德爾認識到該系統存在一個根本缺陷:它是不完備的。也就是說,可以提出一些數學陳述,這些陳述既不能用 ZFC 證偽,也不能用 ZFC 證明。除其他外,一個系統不可能證明自身的相容性。
集合論中最著名的不可判定性例子是 CH。在 1938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哥德爾證明了 CH 不能在 ZFC 中被證偽。保羅·科恩在 25 年後證明了它也不能被證明。因此,使用集合論的通常公理不可能解決 CH。因此,仍然不清楚是否存在既大於自然數又小於實數的集合。
基數不是描述集合大小的唯一概念。例如,從幾何的角度來看,實數軸 ℝ、二維平面(有時稱為 x-y 平面)或三維空間的子集可以被賦予長度、面積或體積。平面中形成邊長為 a 和 b 的矩形的點集具有面積 a ∙ b。計算平面中更復雜子集的面積有時需要其他工具,例如學校教授的積分學。這種方法對於某些複雜集合來說是不夠的。但是許多集合仍然可以使用勒貝格測度來量化,勒貝格測度是一種將長度、面積或體積分配給極其複雜物體的函式。即便如此,仍然可以定義 ℝ 或平面的子集,這些子集過於零碎,以至於根本無法測量。
在二維空間中,一條線(例如圓的周長、有限線段或直線)始終是可測量的,並且其面積為零。因此,它被稱為零測集。零測集也可以在一維中定義。在實數軸上,具有兩個元素的集合——例如 {3, 5}——的測度為零,而諸如 [3, 5] 之類的區間——即三到五之間的實數——的測度為二。
可忽略的集合
零測集的概念在數學中非常有用。通常,一個定理對於所有實數都不成立,但可以證明對於零測集之外的所有實數都成立。這通常足以滿足大多數應用。然而,零測集可能看起來相當大。例如,實數軸內的有理數是一個零測集,即使其中有無窮多個有理數。這是因為任何可數集——或有限集——都是零測集。反之則不然:x-y 平面的具有較大基數的子集不必是可測量的,也不必具有較大的測度。例如,整個平面及其 2ℵ0 個元素具有無限測度。但是,具有相同基數的 x 軸的二維測度(或“面積”)為零,因此是平面的零測集。
這種“可忽略”的集合引發了關於 10 個無限基數大小的基本問題,這些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解答。例如,數學家希望知道一個集合不成為零測集所需的最小大小。所有零測集的族用 𝒩 表示,非零測集的最小基數用 non(𝒩) 表示。由此得出,ℵ0 < non(𝒩) ≤ 2ℵ0,因為任何大小為 ℵ0 的集合都是零測集,並且整個平面的大小為 2ℵ0,並且不是零測集。因此,ℵ1 ≤ non(𝒩) ≤ 2ℵ0,因為 ℵ1 是最小的不可數基數。如果我們假設 CH,那麼 non(𝒩) = 2ℵ0,因為在這種情況下,ℵ1 = 2ℵ0。
我們可以定義另一個基數 add(𝒩),來回答這個問題:使並整合為非零測集的零測集的最小數量是多少?這個數字小於或等於 non(𝒩):如果 A 是一個包含 non(𝒩) 個元素的非零測集,則 A 的所有 non(𝒩) 個單元素子集的並集是非零測集 A。但是,較少數量的零測集(儘管它們不是單元素集)也可能滿足要求。因此,add(𝒩) ≤ non(𝒩) 成立。
基數 cov(𝒩) 是並集產生整個平面的零測集的最小數量。也很容易看出 add(𝒩) 小於或等於 cov(𝒩),因為如前所述,平面是非零測集。
我們還可以考慮 cof(𝒩),𝒩 的基 X 的最小可能大小。也就是說,零測集 X 的集合,它包含每個零測集 A 的超集 B。(這意味著 A 是 B 的子集。)這些無限基數——add(𝒩)、cov(𝒩)、non(𝒩) 和 cof(𝒩)——是零測集族的重要特徵。
對於這四個基數特徵中的每一個,都可以使用不同的“小”或“可忽略”集合的概念來定義類似的特徵。另一個小概念是“稀疏”。稀疏集是包含在無處稠密集的集合的可數並集中的集合,例如平面中圓的周長,或有限或可數多個此類周長。在一維中,正規數形成實數軸上的稀疏集,而其餘的實數,即非正規數,構成零測集。
因此,可以為稀疏集族定義相應的基數特徵:add(ℳ)、non(ℳ)、cov(ℳ) 和 cof(ℳ)。在 CH 下,對於零測集和稀疏集,所有特徵都相同,即 ℵ1。另一方面,使用科恩開發的“力迫法”,數學家肯尼斯·庫寧和阿諾德·米勒在 1981 年證明,不可能在 ZFC 中證明陳述 add(𝒩) = add(ℳ)。換句話說,必須組合以產生非可忽略集合的零測集和稀疏集的數量在證明上是不相等的。
力迫法是一種構造數學宇宙的方法。數學宇宙是滿足 ZFC 公理的模型。為了證明陳述 X 在 ZFC 中不是可反駁的,找到一個 ZFC 和 X 都有效的宇宙就足夠了。類似地,為了證明 X 不能從 ZFC 證明,找到一個 ZFC 成立但 X 失敗的宇宙就足夠了。
具有驚人屬性的數學宇宙
庫寧和米勒使用這種方法構造了一個數學宇宙,該宇宙滿足 add(𝒩) < add(ℳ)。在這個模型中,形成非可忽略集合需要比零測集更多的稀疏集。因此,不可能從 ZFC 證明 add(𝒩) ≥ add(ℳ)。
相比之下,託梅克·巴託辛斯基在三年後發現,逆不等式 add(𝒩) ≤ add(ℳ) 可以 使用 ZFC 證明。這指出了小概念的兩種定義之間的不對稱性。讓我們注意到,如果我們假設 CH,則這種不對稱性是不可見的,因為 CH 意味著 ℵ1 = add(𝒩) = add(ℳ)。
總結:add(𝒩) ≤ add(ℳ) 是可證明的,但 add(𝒩) = add(ℳ) 和 add(𝒩) < add(ℳ) 都不可證明。這與 CH 的效果相同:證明 ℵ1 ≤ 2ℵ0 是微不足道的,但 ℵ1 < 2ℵ0 和 ℵ1 = 2ℵ0 都不可證明。
除了迄今為止定義的基數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基數特徵——𝔟 和 𝔡——它們指的是實數的優勢函式。對於兩個連續函式(其中有 2ℵ0 個)f 和 g,如果對於所有足夠大的 x,不等式 f(x) < g(x) 成立,則稱 f 被 g 支配。例如,諸如 g(x) = x2 之類的二次函式總是支配線性函式,例如 f(x) = 100x + 30。
基數 𝔡 定義為足以支配每個可能的連續函式的連續函式集合的最小可能大小。
這個定義的變體給出了基數 𝔟,即族 B 的最小大小,該族 B 具有不存在支配 B 的所有函式的連續函式的屬性。可以證明 ℵ1 ≤ 𝔟 ≤ 𝔡 ≤ 2ℵ0 成立。
已經證明在我們剛剛定義的 12 個無限基數之間存在幾個額外的不等式。所有這些不等式都總結在西霍恩圖 (Cichoń's diagram) 中,該圖由英國數學家大衛·弗裡姆林在 1984 年引入,並以他的波蘭同事雅採克·西霍恩的名字命名。出於排版原因,小於或等於號被箭頭替換。
.jpg?w=900)
來源:雅各布·凱爾納
還有兩個額外的關係:Add(ℳ) 是 𝔟 和 cov(ℳ) 中較小的一個。同樣,cof(ℳ) 是 𝔡 和 non(ℳ) 中較大的一個。這兩個“依賴”基數在西霍恩圖中用框架標記。因此,該圖包含 12 個不可數基數,其中最多 10 個可以同時不同。
無限可以有多不同?
然而,如果 CH 成立,則 ℵ1(圖中最小的數字)等於 2ℵ0(圖中最大的數字),因此所有條目都相等。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設 CH 為假,那麼它們可能會有很大不同。
幾十年來,數學家們試圖證明西霍恩圖中沒有一個小於或等於關係可以加強為等式。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構造了許多不同的宇宙,在這些宇宙中,他們以各種方式將兩個最小的不可數基數 ℵ1 和 ℵ2 分配給圖中的條目。例如,他們建立了一個宇宙,其中 ℵ1 = add(𝒩) = cov(𝒩),ℵ2 = non(ℳ) = cof(ℳ)。
這項工作使 1980 年代的研究人員能夠確認,對於每對基數,只有圖中指示的關係可以在 ZFC 中證明。更準確地說,對於西霍恩圖(獨立的)條目的每種標記,使用值 ℵ1 和 ℵ2 來遵守圖的不等式,都存在一個宇宙來實現給定的標記。
因此,我們已經知道將近四十年,ℵ1 和 ℵ2 的所有賦值給圖都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兩個以上的值,我們能說什麼呢?例如,所有獨立的條目可以同時不同嗎?一些具有三個特徵的情況已經為人所知 50 年了,在 2010 年代,發現了(或構造了)更多的宇宙,其中西霍恩圖中出現了多達七個不同的基數。
在我們 2019 年與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以色列數學家薩哈龍·謝拉赫 (Saharon Shelah) 合著的論文中,我們構建了一個宇宙,其中西霍恩圖中出現了最大可能數量的不同無限值——即 10 個。然而,在這樣做時,我們使用了比 ZFC 更強大的公理系統,該系統假設存在“大基數”,其存在性在 ZFC 中無法證明。
雖然我們對這個結果感到非常滿意,但我們並不完全滿意。我們又工作了兩年,試圖找到僅使用 ZFC 公理的解決方案。最終,我們與謝拉赫和日本靜岡大學的哥倫比亞數學家迭戈·梅希亞 (Diego Mejía) 一起成功地證明了在沒有這些額外假設的情況下得到的結果。
因此,我們已經證明了實數的 10 個特徵都可以不同。讓我們注意,我們沒有證明在 ℵ1 和連續統之間可以至少、最多或正好有 10 個無限基數。羅伯特·索洛維在 1963 年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事實上,實數集合的大小可能會有很大差異:在 ℵ1 和 2ℵ0 之間可能存在 8 個、27 個或無限多個基數——甚至不可數多個。相反,我們的結果證明,存在數學宇宙,其中 ℵ1 和 2ℵ0 之間的 10 個特定基數最終會變得不同。
這不是故事的結局。正如數學的慣例一樣,許多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新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例如,除了此處描述的基數之外,自 1940 年代以來,還發現了許多其他位於 ℵ1 和連續統之間的無限基數。它們彼此之間的精確關係尚不清楚。區分除西霍恩圖中的那些特徵之外的一些特徵是即將到來的挑戰之一。另一個挑戰是證明 10 個不同值的其他排序是可能的。與兩個值 ℵ1 和 ℵ2 的情況不同,在兩個值的情況下,我們知道所有可能的順序都是一致的,但在所有 10 個值的情況下,我們只能證明兩個不同順序的一致性。所以,誰知道呢,圖中可能仍然隱藏著迄今為止尚未發現的等式——涉及兩個以上的特徵。
本文最初發表在《Spektrum der Wissenschaft》雜誌上,經許可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