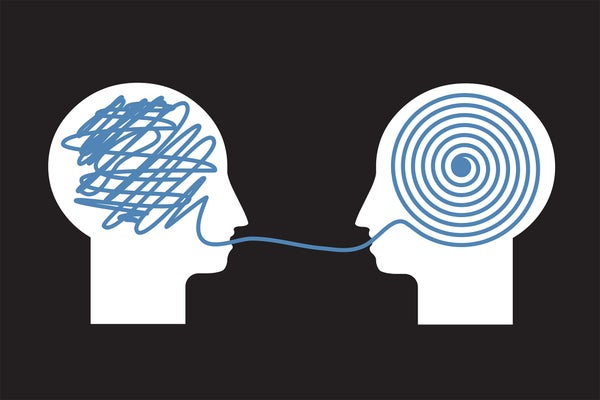一位物理學家、一位哲學家和一位心理學家走進了一間教室。
雖然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笑話的開頭,但這實際上是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索爾·珀爾馬特、哲學家約翰·坎貝爾和心理學家羅布·麥考恩之間獨特合作的起源。他們看到非理性、錯誤資訊和社會政治兩極分化如危險的潮水般上漲,深受觸動,於是在2011年聯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設了一門多學科課程,其目標不高,旨在教導本科生如何思考——更具體地說,如何像科學家一樣思考。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向學生展示如何使用科學工具和技術來解決問題、做出決策以及區分現實與幻想。該課程非常受歡迎,吸引了足夠的興趣持續開辦了十多年(並且還在繼續),同時在其他大學和機構引發了多個衍生課程。
現在,這三位研究人員正透過一本新書《第三個千年思維:在荒謬的世界中創造意義》將他們的資訊傳遞給大眾。他們的時機堪稱完美:自從他們的課程開始以來,我們的世界似乎變得更加不確定和複雜,認知偏差和資訊過載很容易使關於氣候變化、全球疫情和人工智慧的開發和監管等高風險問題的辯論變得模糊不清。但是,人們不必成為學術專家或政策制定者才能從本書中找到價值。從解析每日新聞到治療疾病,在感恩節與意見相左的親戚交談,甚至選擇如何在選舉中投票,《第三個千年思維》都提供了任何人都可以單獨和集體使用的課程,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做出更明智、更好的決策。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業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業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發現和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大眾科學》與珀爾馬特、坎貝爾和麥考恩談論了他們的工作——以及相信邏輯和證據可以拯救世界是否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以下是採訪的編輯稿。]
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是什麼促使你們每個人承擔如此雄心勃勃的專案?
珀爾馬特:2011年,我看到我們的社會正在做出重大決策:“我們應該提高債務上限嗎?”——諸如此類的事情。但令人驚訝的是,我們並沒有以一種非常明智的方式來做。我聽到的關於這些政治決策的對話,與我在實驗室裡與一群科學家共進午餐時的對話不同——不是因為政治,而是因為科學家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風格。我想,“嗯,科學家們是從哪裡學到這些東西的?我們是否有可能闡明這些概念,並以一種人們可以在他們整個生活中應用的方式來教授它們,而不僅僅是在實驗室裡?我們能否讓他們使用最好的認知工具為自己思考,而不是教他們‘只要信任科學家就行了’?”
這就是它的起點。但這並不是全部。如果你把一群物理學家放在一起開個系務會議,他們的表現不一定比其他任何教員更理性,對吧?因此,很明顯,我們真的需要來自其他領域的專業知識,比如約翰在哲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和羅布在社會心理學方面的專業知識。我們實際上貼了一個小標誌,尋找想要幫助開發課程的人。上面寫著,“你是否對我們的社會做出決策感到尷尬?來幫助發明我們的課程;來幫助拯救世界。”
麥考恩:當索爾找到我談論這門課程時,我很高興與他合作。早在2011年,我就對政策辯論的無效性感到焦慮;我花了多年時間研究兩個熱門問題:毒品合法化和同性戀和女同性戀者公開服兵役。我與雙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導者合作,只是想在這些辯論中做一個誠實的中間人,以幫助澄清真相——你知道,“我們實際上知道什麼,我們不知道什麼?”而這兩個問題的辯論質量都非常糟糕,對研究結果的歪曲太多了。因此,當索爾向我提及這門課程時,我立即抓住了這個機會參與其中。
坎貝爾:對我來說,這在哲學上顯然非常有趣。我的意思是,我們正在談論科學如何輸入到決策中。在決策中,總是存在價值問題以及事實問題;關於你想去哪裡,以及我們如何到達那裡的問題;以及關於“科學”可以回答什麼的問題。問“我們能否在決策中區分事實和價值觀?科學對價值觀有什麼啟示嗎?”非常有趣。嗯,可能沒有。科學家總是避免告訴我們價值觀。因此,我們需要了解更廣泛的有效關注如何在決策中與科學成果交織在一起。
其中一些是關於科學如何嵌入社群生活的。你拿一個村莊來說——你有酒吧,你有教堂,你清楚地知道它們是做什麼用的,以及它們在整個社群中是如何運作的。但是科學呢,那是什麼?它只是這種產生電話、電視和各種東西的閃閃發光的東西嗎?它如何融入社群生活?它如何嵌入我們的文明?傳統上,它一直被視為一種“高等教會”式的東西。科學家們確實在象牙塔裡,隨心所欲地做事。然後偶爾,他們會生產出這些小玩意,我們不確定我們是否應該喜歡它們。但我們真的需要對科學如何在更廣泛的社會中發揮作用有一個更健康、更紮實的觀念。
我很高興你提出了事實和價值觀之間的區別。對我來說,這與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區別重疊——“價值觀”感覺更個人化和主觀,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更直接地適用於讀者。而這本書最終是關於個人如何用所謂的科學思維來增強自身能力——大概是為了根據他們的個人價值觀過上最好的生活。但這與你剛才提出的另一個主張,即科學可能根本無法告訴我們任何關於價值觀的事情,又如何協調一致呢?
珀爾馬特:嗯,我認為約翰想要表達的是:即使我們開發出所有這些思考事實的方法,我們也不想停止思考價值觀,對吧?這裡的一點是,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我們在思考價值觀方面共同取得了進步。我們必須繼續互相交談。但將價值觀和事實分開仍然非常有幫助,因為每種都需要略有不同的思維方式,你希望人們能夠兩者兼顧。
麥考恩:沒錯。科學家不能告訴我們,實際上也不應該告訴我們,要持有何種價值觀。當科學家試圖這樣做時,就會惹上麻煩。我們在書中談到了科學有時會發生的“病態”,以及這些病態是如何被基於價值觀的思維所驅動的。關於價值觀,科學擅長的是澄清價值觀在哪裡以及如何衝突,以便在公共政策分析中,你可以告知權衡取捨,以確保辯論中的利益相關者從經驗上理解其各種結果如何在推進某些價值觀的同時阻礙其他價值觀。通常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找到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這些權衡取捨並減少相互衝突的價值觀之間摩擦的解決方案。
讓我們明確一點:當我們談論價值觀時,我們有時會說得好像人們要麼是這樣,要麼是那樣。你知道,有人可能會問,“你是贊成還是反對‘自由’?”但實際上,每個人都珍視自由。這只是一個程度問題,我們在這類事情的排名上存在差異。我們都在尋找某種同時追求多種價值觀的方法,我們需要其他人來幫助我們實現目標。
珀爾馬特:讓我們記住,即使在我們自己內心,對於我們個人價值觀的排名也並不一致,它們往往會根據情況發生很大波動。
我喜歡我們的討論現在如何反映了這本書的風格:輕鬆、平易近人,但也毫不退縮地談論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在書中,你們試圖給讀者提供一個“工具包”,以便駕馭這些事物。這很棒,但對於可能認為這是一本科學注入的自助書籍,為他們提供一些關於如何提高理性思維的簡單規則的讀者來說,這可能具有挑戰性。這讓我想到:如果你們必須以某種方式將這本書的資訊簡化為類似便條卡上的一系列要點,那會是什麼?工具包中最基本的工具是什麼?
坎貝爾:這可能有點諷刺,但我最近在某個地方讀到,ChatGPT 等人工智慧程式真正出錯的地方在於不提供來源。大多數這些工具不會告訴你他們為自己的輸出使用了什麼證據。你可能會認為,當然,我們應該總是展示我們為我們即將說的任何話提供的證據。但實際上,我們做不到。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記得我們所知道的一半事情的證據。我們通常可以回憶起來的是,我們認為某個斷言為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們認為它的機率有多大。保持對這一點的跟蹤是一種有價值的思維習慣:如果你要根據你可能有的任何信念採取行動,你需要知道你可以多大程度地堅持這種信念。
珀爾馬特:我們在書中花了很多時間討論這個問題,因為它讓你看到,這個世界幾乎沒有確定性的東西向我們走來。即使我們對某件事非常確定,我們也只是非常確定,並且對某些事情與我們認為或期望的相矛盾的可能性有一種感覺,這其中有真正的效用。許多人一直自然而然地這樣做,思考在他們最喜歡的運動隊上下注的機率,或者思考陣雨破壞野餐的可能性。承認不確定性可以讓你的自我在正確的位置上。你的自我最終應該依附於擅長知道你對某些事實的信任有多強或多弱,而不是總是正確。需要總是正確是一種非常有問題的對待世界的方式。在書中,我們將其比作雙腿僵硬地站在滑雪板上滑下山坡;如果你從不改變姿勢來轉彎和減速,你可能會滑得非常快,但通常你不會走太遠就會摔倒!因此,你需要能夠操縱和調整以跟蹤你真正知道的是什麼,而不是你不知道的是什麼。這就是實際到達你想去的地方的方式,這也是如何與可能不同意你觀點的人進行有益對話的方式。
麥考恩:而這種共同努力的感覺很重要,因為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些思維習慣不僅僅關乎你的個人決策;它們也關乎科學在民主制度中如何運作。你知道,科學家最終不得不與他們不同意的人一起工作。他們培養了一些共同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因為僅僅成為一個“更好”的思考者是不夠的;即使是那些受過這些方法良好訓練的人也會犯錯誤。因此,你還需要在公共層面擁有這些習慣,讓其他人保持你的誠實。這意味著與那些不同意你觀點的人互動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那是你發現自己何時犯錯的方式。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你會改變你的想法。但這會改善你對自身觀點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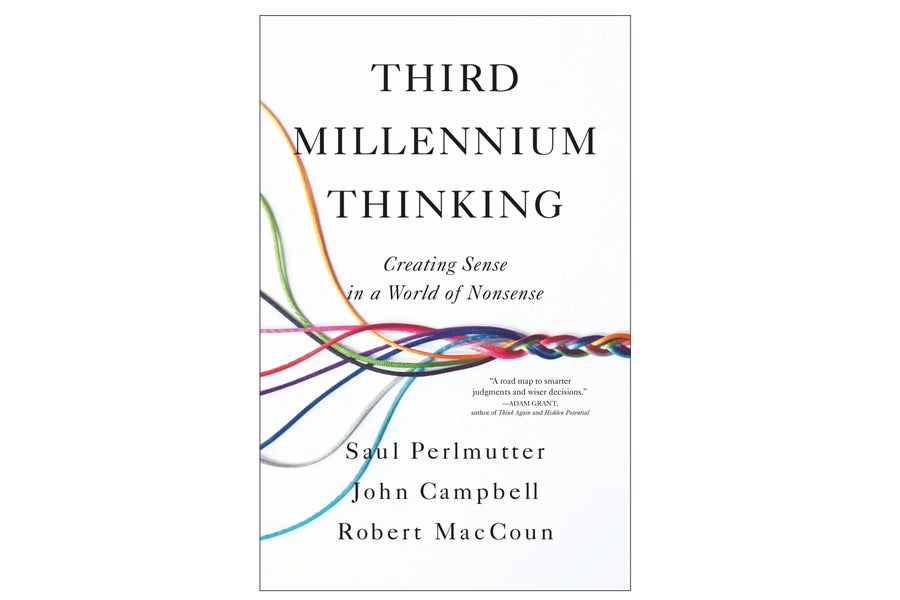
因此,總結一下
嘗試對你信念的信心進行排名。
嘗試根據新證據更新你的信念,不要害怕(暫時)犯錯。
嘗試與持有與你不同信念的其他人進行有成效的互動。
我認為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前三名”列表!但是,請原諒我的憤世嫉俗,你是否擔心其中一些可能會顯得相當古樸?我們在開頭提到,這個專案實際上始於2011年,距今不過十多年。然而,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那段時間的社會和技術變革現在已經有效地將我們置於不同的境地,不同的世界。至少在我看來,現在平均而言,與10年前相比,持有不同信念和價值觀的人們更難進行愉快、富有成效的對話。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真的可以透過每個人聚在一起交談來解決嗎?
坎貝爾:我同意你的看法,這種憤世嫉俗現在很普遍。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如何跨越根本分歧進行對話,所以現在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試圖轉變那些持有不同觀點的人是毫無意義的。但另一種選擇是透過脅迫來管理社會。僅僅用暴力征服來擊垮人們並不是一個長期的可行解決方案。如果你要脅迫,你至少必須展示你的工作。你必須與其他人互動,並解釋你為什麼認為你的政策是好的。
麥考恩:你可以將憤世嫉俗視為懷疑主義和悲觀主義的可怕腐蝕性混合物。在另一個極端,你有輕信,它與樂觀主義相結合,會導致一廂情願的想法。這實際上也沒有幫助。在書中,我們談到了索爾的一個見解,即科學家傾向於將懷疑主義與樂觀主義結合起來——我認為這種組合在我們的社會中並不普遍培養。科學家是懷疑的,而不是輕信的,但他們是樂觀的,而不是悲觀的:他們傾向於假設問題有解決方案。因此,圍坐在桌子旁的科學家更有可能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不是哀嘆它有多麼糟糕。
珀爾馬特:這是我們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我認為有幾個要素對於傳遞它很重要。一個是,當你看到我們社會的領導人時,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失望。他們在結構上現在已經陷入困境,他們似乎甚至無法公開表達他們的信念,更不用說在有爭議的問題上找到真正的妥協方案了。與此同時,你可以找到許多“公民大會”活動的例子,在這些活動中,隨機選擇的普通人完全不同意,並且支援政治光譜的對立面,他們坐在一起,比他們的社會政治領導人更能進行文明、周到的對話。這讓我認為,這個國家的大部分人(但不是全部!)可以彼此進行非常合理的對話。因此,顯然我們有一個機會,我們還沒有利用它來在結構上找到方法來增強這些對話,而不僅僅是領導人試圖為我們行動。這值得樂觀。另一個是,每日新聞將世界描繪成一個非常可怕和消極的地方——但我們知道,每日新聞並沒有提供一個非常好的代表性的觀點來反映世界的真實狀態,尤其是在過去幾十年中人類福祉的巨大改善方面。
因此,我覺得許多人生活在“危機”模式中,因為他們總是消費新聞,這些新聞每時每刻都在向我們呈現危機,並用楔子問題分裂我們。我認為,在尋找再次對話的方式中可以找到樂觀情緒。正如約翰所說,那是唯一的選擇:嘗試與人們合作,直到你們一起學到一些東西,而不是僅僅試圖獲勝,然後讓一半人口不高興。
坎貝爾:我們也許是地球上最具部落性的物種,但我們也可能是地球上最令人驚歎的靈活和合作的物種。正如索爾所說,在這些幾乎是市政廳式的審議性公民大會中,你會看到這種合作能力湧現出來,即使是在那些意見嚴重分歧並且[屬於]對立部落的人們之間——因此,一定有辦法放大這種能力,並擺脫被鎖定在這些部落分裂中的狀態。
麥考恩:重要的是要記住,關於合作的研究表明,你不需要每個人都合作才能獲得好處。你確實需要一個臨界質量,但你永遠不會讓每個人都合作,所以你不應該浪費時間試圖達到100%。[政治學家]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和其他研究合作進化的人已經表明,如果合作者能夠找到彼此,他們就可以開始蓬勃發展並開始吸引其他合作者,並且他們可以在面對那些不合作或試圖破壞合作的人時變得更加強大。因此,以某種方式獲得那個臨界質量可能是你能期望的最好的結果。
我相信沒有人注意到,當我們討論大規模社會合作時,我們也正處於美國——表面上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的選舉年。當然,這裡的部分等式是用基本的善意和謙遜來打破隔閡:愛你的鄰居,找到共同點,等等。但是投票呢?科學決策是否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關於那裡的“最佳實踐”的指導?
珀爾馬特:嗯,顯然我們希望這能夠超越選舉年。但總的來說,你應該避免僅僅基於恐懼做出決定——包括投票。現在不是世界上應該讓恐懼成為驅動我們個人或集體行動的主要因素的時候。我們的大部分恐懼會分裂我們,然而我們的大部分力量都在於共同努力解決問題。因此,一個基本的事情是不讓自己因為恐懼而慌亂地投票給任何人或任何事。但另一個是尋找那些使用和反映科學思維方式的領導人,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你願意承認自己可能犯錯,你受證據約束,並且如果事實證明你正在執行一個糟糕的計劃,你能夠改變主意。不幸的是,我們很少看到這種情況。
坎貝爾:目前我們擁有大量的言論自由——每個人都可以進入某種社交媒體,向全國解釋他們的觀點。但我們似乎已經忘記了,言論自由的全部意義在於檢驗思想。那就是為什麼它看起來如此美好:透過言論自由,可以產生、討論和檢驗新的思想。但是,檢驗你自由表達的思想的想法已經從文化中消失了。我們真的需要重新調整我們如何教授和談論言論自由及其價值。你知道,它不僅僅是一個目的本身,對吧?
麥考恩:讓我們也注意一些歷史教訓。對於許多如此兩極分化和分裂的問題,很可能最終的結果是雙方都沒有完全正確,並且存在一些我們大多數人甚至沒有人想到的第三種可能性。這種情況在科學中經常發生,每一個勝利的見解通常都是暫時的,直到下一個更好理論或證據出現。同樣,如果我們不能超越爭論我們目前對這些問題的概念,我們就會把自己困在這個狹小的概念空間區域,而解決方案可能在某個外部。這是我們在書中談到的眾多認知陷阱之一。與其固守陣地,不如對不確定性和實驗持更開放的態度:我們測試針對問題的某些政策解決方案,如果它不起作用,我們準備迅速做出調整並嘗試其他方法。
也許我們可以實踐我們在這裡宣揚的東西,即進行循證測試和糾正偏差,並擺脫各種認知陷阱的想法。在你們創作這本書的過程中,你們是否發現並反思過你們可能有的任何非理性思維習慣?是否有過你選擇固守陣地,但你錯了,並且你不情願地進行了調整的情況?
麥考恩:是的,在書中,我們給出了我們自己個人錯誤的例子。我自己的研究中的一個例子涉及可重複性危機和人們參與證實偏差。我寫了一篇綜述論文,總結了似乎表明將毒品非刑罪化——即取消對毒品的刑事處罰——不會導致使用量增加的證據。寫完之後,我有一個新的機會來檢驗這個假設,我查看了來自義大利的資料,在20世紀70年代,義大利基本上將個人擁有少量所有毒品非刑罪化了。然後在1990年他們又重新將它們定為刑事犯罪。然後在1993年他們又重新非刑罪化。所以這就像一個完美的機會。資料表明,當他們重新實施處罰時,與毒品相關的死亡人數實際上下降了,而當取消處罰時,死亡人數又回升了。這與我已經建立聲譽的觀點完全相反!所以,好吧,我個人有偏見,對吧?這真的是我去做更多研究,深入挖掘義大利案例的唯一原因,因為我不喜歡這些發現。因此,在同一時間跨度內,我查看了西班牙(一個非刑罪化但沒有重新定為刑事犯罪的國家)和德國(一個在那段時間從未非刑罪化的國家),這三個國家都顯示出相同的死亡模式。這表明,可疑的死亡模式實際上與處罰無關。現在,我認為這導致了正確的結論——當然,我的原始結論!但重點是:我很慚愧地承認,我陷入了證實偏差的陷阱——或者,確切地說,是它的近親,稱為否定偏差,在這種偏差中,你對似乎與你的信念相悖的證據更加苛刻。這絕對是一個具有教育意義的時刻。
坎貝爾:承認這些事情並做出必要的轉變需要很大的勇氣。影響我們許多人的一個認知陷阱是所謂的內隱偏見盲點,在這種盲點中,你在發現別人的偏見方面可能非常敏銳和有洞察力,但對自己卻不然。你通常可以在瞬間發現別人的某種偏見。但是當你審視自己時會發生什麼?通常的反應是,“不,我不會做那種事!”你知道,我一定已經審查了成百上千份學生的入學申請或教師職位搜尋,但我從未發現自己有任何偏見,一次也沒有。“我只是直接看申請,”對吧?但這不可能總是真的,因為最容易被愚弄的人是你自己!意識到這一點可能是一種啟示。
珀爾馬特:這真的說明了本書的一個關鍵點:我們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來與那些我們不同意的人合作——因為消除你自身偏見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找到一個不同意你觀點並且非常有動力證明你是錯的人。這很難,但你真的需要忠誠的反對派。例如,回想起來,導致發現暗能量的宇宙膨脹測量的重大競賽是在我的團隊和另一個團隊之間進行的。有時,我的同事和我會在我們結束觀測離開望遠鏡時,看到另一個團隊的成員出現來進行他們的觀測,知道兩個團隊都在追逐同一件事,這讓人感到不舒服。另一方面,這種競爭確保了我們每個人都會嘗試找出另一個團隊是否在犯錯,並且它極大地提高了我們集體對結果的信心。但這僅僅有兩個對立的方面是不夠的——你還需要讓他們彼此接觸的方式。
我意識到我無意中把可能最基本的問題留到了最後。到底什麼是“第三個千年思維”?
珀爾馬特:沒關係,實際上我們也把解釋這個問題留到了本書的最後一章!
麥考恩:第三個千年思維是關於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一個重大轉變。我們都對科學之前的漫長千年可能是什麼樣子有一種感覺,我們都知道,隨著現代科學時代的出現,逐漸出現了巨大的進步——從各種古代文明的實踐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所有這些思維方式的轉變都導致了驚人的科學革命,這場革命在我們這個直到20世紀末才結束的第二個千年裡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但最近,也出現了對科學的失望。而且,科學有時只是權勢者的婢女,以及科學家有時會運用比他們應得的更多的權威來推進他們自己的個人專案和政治,這些擔憂是有道理的。有時科學會變得病態;有時它會失敗。
第三個千年思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承認科學的歷史缺陷,但也承認其自我糾正的能力,我們今天正在看到其中的一些能力。我們認為,這正在引導我們進入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科學變得不那麼等級森嚴。它變得更加跨學科和基於團隊,並且在某些情況下,對於普通人來說,更有可能有意義地參與其中——想想所謂的公民科學專案。科學也變得更加開放,研究人員必須透過使其資料和方法更容易獲得來展示他們的工作,以便其他人可以獨立檢查它。我們希望這些型別的變化正在使科學家變得更加謙遜:那種“是的,我有博士學位,所以你聽我的”的態度,對於重大的、有爭議的政策問題來說,不一定再奏效了。你需要更審慎的諮詢,讓普通人可以參與其中。科學家確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堅守自己的崗位,而不是僅僅根據他們的資歷來聲稱權威——權威來自使用的方法,而不是來自資歷。
我們看到這些都有聯絡,它們有可能促進一種新的科學方法和成為科學家的新的方式,這就是第三個千年思維的意義所在。
坎貝爾:在新冠疫情期間,我認為我們都很悲哀地熟悉了個人公民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與科學家的權威相對立的觀點。你知道,“科學家是一個會指揮你、削弱你的自由並給你注射摻有精神控制奈米機器人的疫苗的人”等等。這真是太可惜了。當人們這樣使用或看待科學時,這是非常令人衰弱的。或者,你可能會說,“嗯,我不是科學家,我不會做數學,所以我只會相信並做他們告訴我的任何事情。”那真的是放棄你的自由。科學應該是個人力量的促成者,而不是對你自由的威脅。第三個千年思維是關於實現這一目標,讓儘可能多的人透過使用科學思維來獲得力量——自我賦權。
珀爾馬特:沒錯。我們正試圖幫助人們看到,我們現在在世界各地看到的這種趨勢組合實際上是一個非常肥沃的機會,可以帶來重大、有意義的積極變化。如果我們傾向於此,它可以使我們在通往真正偉大的千年的長期道路上處於非常有利的位置。即使目前有所有這些其他力量需要擔心,透過將科學文化中的工具、思想和過程應用於我們生活的其他部分,我們可以在邁向更光明、更美好的未來時順風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