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你對自己的看法是扭曲的。
你的“自我”就像一本開啟的書一樣擺在你面前。只需窺視內部並閱讀:你是誰,你的喜好和厭惡,你的希望和恐懼;它們都在那裡,準備被理解。這種觀念很流行,但可能完全是錯誤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我們並沒有特權去了解我們是誰。當我們試圖準確評估自己時,我們實際上是在霧裡摸索。
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家艾米麗·普羅寧,她專門研究人類的自我認知和決策,將對特權訪問的錯誤信念稱為“內省錯覺”。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是扭曲的,但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結果,我們的自我形象與我們的行為關係出奇地小。例如,我們可能絕對確信自己富有同情心和慷慨,但仍然在寒冷的一天徑直走過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根據普羅寧的說法,這種扭曲觀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不想吝嗇、傲慢或自以為是,所以我們假設我們不是任何這些東西。作為證據,她指出了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不同看法。我們毫不費力地認識到我們的辦公室同事對另一個人是多麼的偏見或不公平。但我們沒有考慮到我們可能會以幾乎相同的方式行事:因為我們打算在道德上是善良的,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想到我們自己也可能是有偏見的。
普羅寧在許多實驗中評估了她的論點。其中,她讓她的研究參與者完成一項測試,該測試涉及將面孔與個人陳述相匹配,這些陳述本應評估他們的社交智力。之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被告知他們失敗了,並被要求指出測試程式中的弱點。儘管受試者的意見幾乎肯定是帶有偏見的(他們不僅被認為測試失敗了,而且還被要求批評它),但大多數參與者表示他們的評估是完全客觀的。在評判藝術作品時情況也大致相同,儘管使用有偏見的策略評估繪畫質量的受試者仍然認為他們自己的判斷是公正的。普羅寧認為,我們天生就被設定為掩蓋自己的偏見。
“內省”這個詞僅僅是一個漂亮的隱喻嗎?會不會是我們並沒有真正地審視自己,正如這個詞的拉丁詞根所暗示的那樣,而是在產生一個奉承的自我形象,否認我們所有人都有的缺點?關於自我認知的研究已經為這個結論提供了很多證據。儘管我們認為我們正在清晰地觀察自己,但我們的自我形象受到仍然無意識的過程的影響。
2. 你的動機通常對你來說是一個完全的謎。
人們對自己有多瞭解?在回答這個問題時,研究人員遇到了以下問題:要評估一個人的自我形象,就必須知道這個人到底是誰。調查人員使用各種技術來解決這些問題。例如,他們將測試物件的自我評估與受試者在實驗室情況或日常生活中的行為進行比較。他們可能會要求其他人,例如親戚或朋友,也對受試者進行評估。他們還使用特殊方法探測無意識的傾向。
為了衡量無意識的傾向,心理學家可以應用一種稱為內隱關聯測試 (IAT) 的方法,該方法由華盛頓大學的安東尼·格林沃爾德和他的同事在 20 世紀 90 年代開發,用於揭示隱藏的態度。從那時起,人們設計了許多變體來檢查焦慮、衝動性和社交能力等特徵。該方法假設瞬時反應不需要反思;因此,個性的無意識部分會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實驗者試圖確定與某人相關的詞語與某些概念的聯絡有多緊密。例如,在一項研究中,當螢幕上出現描述外向性等特徵的詞語(例如“健談”或“精力充沛”)時,參與者被要求儘快按下按鍵。當他們在螢幕上看到與自己相關的詞語(例如他們自己的名字)時,他們也被要求按下同一個按鍵。當出現內向特徵(例如“安靜”或“內向”)或當該詞語涉及其他人時,他們應該按下不同的按鍵。當然,在許多次測試執行中,詞語和按鍵組合被切換了。例如,如果當與參與者相關的詞語跟隨“外向”出現時,反應更快,那麼可以假設外向性可能是一個人自我形象的組成部分。
這種“內隱”的自我概念通常與透過問卷調查獲得的自我評估只有微弱的對應關係。人們在調查中傳達的形象與他們對情感色彩濃厚的詞語的閃電般的反應幾乎無關。一個人的內隱自我形象通常可以很好地預測他或她的實際行為,尤其是在涉及緊張或社交能力時。另一方面,問卷調查可以更好地瞭解諸如責任心或對新體驗的開放性等特質。德國明斯特大學的心理學家米特亞·巴克解釋說,旨在引發自動反應的方法反映了我們個性的自發或習慣性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責任心和好奇心需要一定程度的思考,因此可以透過自我反省更容易地進行評估。
3. 外在表現告訴人們很多關於你的資訊。
許多研究表明,我們最親近的人往往比我們自己更瞭解我們。正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家西米內·瓦齊爾所表明的那樣,特別是兩個條件可能使其他人更容易認識到我們真正的身份:首先,當他們能夠從外在特徵中“讀出”一種特質時;其次,當一種特質具有明顯的正面或負面效價時(例如,智力和創造力顯然是令人嚮往的;不誠實和自我中心則不是)。當涉及到更中性的特徵時,我們對自己的評估與他人的評估最接近。
通常最容易被他人解讀的特徵是那些強烈影響我們行為的特徵。例如,天生善於交際的人通常喜歡說話和尋求陪伴;不安全感通常表現為諸如絞著雙手或轉移視線等行為。相比之下,沉思通常是內在的,在自己的思想範圍內展開。
我們經常對我們對他人的影響視而不見,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面部表情、手勢和肢體語言。我幾乎沒有意識到我的眨眼表明壓力,或者我的姿勢塌陷暴露了某件事對我來說有多麼沉重。因為觀察自己是如此困難,我們必須依靠他人的觀察,尤其是那些瞭解我們的人的觀察。除非別人讓我們知道我們如何影響他們,否則很難知道我們是誰。

沒有安全感?誰,我?!我們常常對我們對他人的影響了解甚少。圖片來源: Terry Mcclendon Getty Images
4. 保持一定距離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瞭解自己。
寫日記、暫停進行自我反省以及與他人進行探究性對話有著悠久的傳統,但這些方法是否能讓我們瞭解自己還很難說。事實上,有時做相反的事情——例如放手——更有幫助,因為它提供了一些距離。2013 年,現在在多倫多大學的埃裡卡·卡爾森回顧了關於正念冥想是否以及如何提高自我認知的文獻。她指出,它透過克服兩個巨大的障礙來提供幫助:扭曲的思維和自我保護。正念的練習教會我們允許我們的想法簡單地飄過,並儘可能少地認同它們。畢竟,想法“只是想法”,而不是絕對的真理。通常,以這種方式走出自我,簡單地觀察思想在做什麼,可以培養清晰度。
深入瞭解我們的無意識動機可以增強情緒健康。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弗里德里希-亞歷山大大學的奧利弗·C·舒爾特海斯表明,隨著我們的意識目標和無意識動機變得更加一致或協調,我們的幸福感往往會增長。例如,如果這些目標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我們就不應該為了從事一份能給我們金錢和權力的職業而拼命工作。但是我們如何實現這種和諧呢?例如,透過想象。嘗試儘可能生動和詳細地想象一下,如果你最熱切的願望成真,事情會變成什麼樣。它真的會讓你更快樂嗎?我們經常屈服於過度追求高目標的誘惑,而沒有考慮到實現雄心勃勃的目標所需的所有步驟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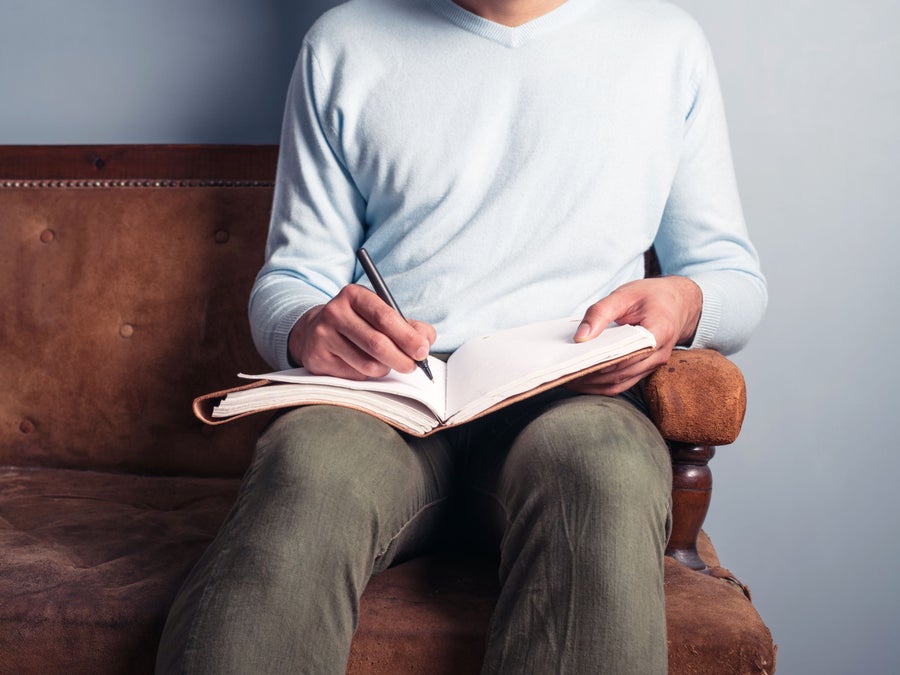
透過日記進行自我發現?那些以一定距離審視自己的人——例如,在獨處時——可能會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5. 我們常常認為自己比實際更擅長某件事。
你熟悉鄧寧-克魯格效應嗎?它認為,人越無能,就越意識不到自己的無能。這種效應以密歇根大學的大衛·鄧寧和紐約大學的賈斯汀·克魯格的名字命名。
鄧寧和克魯格給他們的測試物件佈置了一系列認知任務,並要求他們估計自己做得有多好。充其量,25% 的參與者或多或少地以現實的態度看待自己的表現;只有少數人低估了自己。在測試中得分最差的四分之一受試者真的沒有達到目標,他們極大地誇大了自己的認知能力。吹噓和失敗是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正如研究人員強調的那樣,他們的工作突出了自我認知的普遍特徵:我們每個人都傾向於忽視自己的認知缺陷。倫敦大學學院的心理學家阿德里安·弗納姆表示,感知智商和實際智商之間的統計相關性平均只有 0.16——委婉地說,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表現。相比之下,身高和性別之間的相關性約為 0.7。
那麼,為什麼潛在表現和實際表現之間的差距如此之大呢?難道我們都不想現實地評估自己嗎?這肯定會避免我們浪費大量精力,或許還能避免一些尷尬。答案似乎是,適度誇大自尊心是有一定好處的。根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心理學家雪萊·泰勒和華盛頓大學的喬納森·布朗的評論,玫瑰色的眼鏡往往會增加我們的幸福感和表現。另一方面,患有抑鬱症的人傾向於在自我評估中保持殘酷的現實主義。一個美化的自我形象似乎可以幫助我們度過日常生活的起伏。
6. 貶低自己的人更頻繁地經歷挫折。
儘管我們大多數同齡人都對自己的誠實或智力抱有過於積極的看法,但有些人卻遭受著相反的扭曲:他們貶低自己和自己的努力。童年時期經歷的蔑視和貶低,通常與暴力和虐待有關,會引發這種消極情緒——反過來,這會限制人們可以完成的事情,導致不信任、絕望甚至自殺念頭。
認為具有負面自我形象的人正是那些想要過度補償的人似乎是合乎邏輯的。然而,正如與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威廉·斯旺合作的心理學家所發現的那樣,許多被自我懷疑折磨的人尋求對他們扭曲的自我認知的確認。斯旺在一項關於婚姻幸福感的研究中描述了這種現象。他詢問夫妻雙方自己的優點和缺點,他們感受到伴侶支援和重視的方式,以及他們在婚姻中的幸福程度。正如預期的那樣,那些對自身態度更積極的人發現,他們從另一半那裡獲得的讚揚和認可越多,他們在關係中就越滿意。但是,那些習慣性地挑剔自己的人,當他們的伴侶將他們的負面形象反映給他們時,他們在婚姻中會感到更安全。他們沒有要求尊重或讚賞。相反,他們想聽到的正是他們自己對自己的看法:“你很無能。”
斯旺基於這些發現提出了他的自我驗證理論。該理論認為,我們希望別人像我們看待自己一樣看待我們。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實際上會激怒他人對他們做出負面回應,以證明他們是多麼的毫無價值。這種行為不一定是受虐狂。它是對連貫性渴望的症狀:如果其他人以確認我們自我形象的方式回應我們,那麼世界就應該是這樣。
同樣,那些認為自己是失敗者的人會竭盡全力不成功,從而積極地促成自己的失敗。他們會錯過會議,習慣性地忽視分配的工作,並與老闆發生衝突。斯旺的方法與鄧寧和克魯格的過度估計理論相矛盾。但兩派可能都是正確的:過度膨脹的自我當然很常見,但負面的自我形象也並不少見。
7. 你在不知不覺中欺騙自己。
根據一項有影響力的理論,我們自我欺騙的傾向源於我們渴望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為了顯得有說服力,我們自己必須相信自己的能力和真實性。支援這一理論的觀察是,成功的操縱者通常都非常自負。例如,優秀的銷售人員會散發出一種具有感染力的熱情;相反,那些懷疑自己的人通常不擅長甜言蜜語。實驗室研究也支援這一點。在一項研究中,如果參與者在面試中能令人信服地聲稱自己在智商測試中取得了優異成績,他們就會獲得報酬。候選人在表現中付出的努力越多,他們自己就越相信自己擁有高智商,即使他們的實際分數或多或少是平均水平。
我們的自我欺騙已被證明是相當多變的。我們經常靈活地調整它們以適應新的情況。布朗大學的史蒂文·A·斯洛曼和他的同事證明了這種適應性。他們的受試者被要求儘可能快地將游標移動到計算機螢幕上的一個點。如果參與者被告知,在這項任務中高於平均水平的技能反映了高智商,他們會立即專注於這項任務並做得更好。他們似乎並沒有真正認為自己付出了更多努力——研究人員將此解釋為成功自我欺騙的證據。另一方面,如果測試物件確信只有笨蛋才能在如此愚蠢的任務中表現良好,他們的表現就會急劇下降。
但是,自我欺騙甚至可能嗎?我們能否在某種程度上瞭解自己,而又沒有意識到它?當然可以!實驗證據涉及以下研究設計:向受試者播放人類聲音的錄音帶,包括他們自己的聲音,並要求他們發出訊號表明他們是否聽到自己的聲音。識別率會根據錄音帶的清晰度和背景噪音的大小而波動。如果同時測量腦電波,則閱讀中的特定訊號可以肯定地表明參與者是否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大多數人聽到自己的聲音時都會感到有些尷尬。在一項經典研究中,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魯本·古爾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哈羅德·薩凱姆利用了這種沉默寡言,將測試物件的陳述與他們的腦部活動進行了比較。瞧,活動經常發出“那是我!”的訊號,而受試者並沒有公開地將某個聲音識別為他們自己的聲音。此外,如果調查人員威脅到參與者的自我形象——例如,告訴他們他們在另一項(不相關的)測試中得分很差——他們就更不容易認出自己的聲音。無論哪種方式,他們的腦電波都講述了真實的故事。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評估了學生在練習測試中的表現,該測試旨在幫助學生評估自己的知識,以便他們能夠填補空白。在這裡,受試者被要求在設定的時間限制內完成儘可能多的任務。鑑於練習測試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他們需要的資訊,他們作弊幾乎沒有意義;相反,人為抬高的分數可能會導致他們放鬆學習。那些試圖透過使用超出分配完成時間的時間來提高分數的人只會傷害自己。
但是,許多志願者確實這樣做了。無意識地,他們只是想看起來不錯。因此,作弊者解釋說他們超時是因為他們分心了,並且想要彌補失去的時間。或者他們說,他們偽造的結果更接近他們的“真正潛力”。研究人員認為,這種解釋混淆了因果關係,人們錯誤地認為,“聰明人通常在考試中表現更好。因此,如果我只是透過比允許的時間多花一點時間來操縱我的考試分數,我也是聰明人之一。”相反,如果人們被告知表現良好表明患精神分裂症的風險更高,他們的表現就會不那麼勤奮。研究人員將這種現象稱為診斷性自我欺騙。
8. “真我”對你有好處。
大多數人認為他們有一個堅實的本質核心,一個真我。他們真正的身份主要體現在他們的道德價值觀中,並且相對穩定;其他偏好可能會改變,但真我始終不變。德克薩斯 A&M 大學的麗貝卡·施萊格爾和約書亞·希克斯及其同事研究了人們對真我的看法如何影響他們對自己的滿意度。研究人員要求測試物件記錄他們日常生活的日記。結果表明,當參與者做了道德上可疑的事情時,他們會感到與自己最疏遠:當他們不誠實或自私時,他們特別不確定自己實際上是誰。實驗也證實了自我與道德之間的關聯。當測試物件被提醒早期的不當行為時,他們對自己的確定性會受到打擊。
耶魯大學的喬治·紐曼和約書亞·諾布發現,人們通常認為人類內心深處都懷有一個善良的真我。他們向受試者展示了不誠實的人、種族主義者等人的案例研究。參與者普遍將案例研究中的行為歸因於環境因素,例如艱難的童年——這些人的真正本質肯定與此不同。這項工作表明,我們傾向於認為,在人們的內心深處,他們會追求道德和善良。
紐曼和諾布的另一項研究涉及“馬克”,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但他仍然被其他男人所吸引。研究人員試圖瞭解參與者如何看待馬克的困境。對於保守的測試物件來說,馬克的“真我”不是同性戀;他們建議他抵制這種誘惑。那些持更自由觀點的人認為他應該出櫃。然而,如果馬克被描繪成一個世俗人文主義者,他認為同性戀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想到同性伴侶時卻有負面情緒,保守派很快將這種不情願視為馬克真我的證據;自由派則將其視為缺乏洞察力或世故的證據。換句話說,我們聲稱是另一個人個性的核心實際上根植於我們自己最珍視的價值觀。“真我”原來是一把道德標尺。
對真我是道德的這種信念可能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將個人進步而不是個人缺陷與他們的“真我”聯絡起來。顯然,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積極地提升對自己的評價。安大略省威爾弗裡德·勞裡埃大學的安妮·E·威爾遜和安大略省滑鐵盧大學的邁克爾·羅斯在幾項研究中表明,我們傾向於將更多的負面特徵歸因於過去的自己——這讓我們現在看起來更好。根據威爾遜和羅斯的說法,人們回溯得越遠,他們的性格描述就越負面。儘管進步和改變是正常成熟過程的一部分,但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人已經成為“真正的自己”感覺很好。
假設我們有一個堅實的身份核心可以降低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的複雜性。我們周圍的人扮演著許多不同的角色,他們的行為前後不一致,同時又在不斷發展。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朋友湯姆和莎拉明天將與今天完全一樣,而且他們基本上都是好人——無論這種看法是否正確。
沒有對真我的信念,生活甚至可以想象嗎?研究人員透過比較不同的文化來研究這個問題。對真我的信念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很普遍。一個例外是佛教,它宣揚穩定的自我不存在。未來的佛教僧侶被教導要看穿自我的虛幻性——它總是處於變化之中,並且完全可塑。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尼娜·斯特羅明格和她的同事想知道這種觀點如何影響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對死亡的恐懼。他們向大約 200 名西藏俗人和 60 名佛教僧侶發放了一系列問卷和情景。他們將結果與美國基督徒和非宗教人士的結果,以及印度教徒的結果(他們與基督徒非常相似,認為靈魂的核心,或梵我,賦予人類身份)進行了比較。佛教徒的常見形象是他們非常放鬆,完全是“無私”的人。然而,西藏僧侶越不相信穩定的內在本質,他們就越有可能害怕死亡。此外,在一個假設的情景中,放棄某種藥物可以延長另一個人的生命,他們明顯更加自私。近四分之三的僧侶反對虛構的選擇,遠遠超過美國人或印度教徒。自私自利、恐懼死亡的佛教徒?在另一篇論文中,斯特羅明格和她的同事將真我的概念稱為“充滿希望的幻想”,儘管它可能是有用的。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難以動搖的概念。

佛教徒認為自我是一種幻覺。然而,研究表明,這種信念比相信真我更容易讓人產生對死亡的恐懼。圖片來源: Gavin Gough Getty Images
9. 沒有安全感的人往往表現得更道德。
沒有安全感通常被認為是缺點,但它並非完全不好。對他們是否具有某些積極特質感到不安全的人往往會試圖證明他們確實具有這些特質。例如,那些不確定自己是否慷慨的人更有可能向慈善事業捐款。這種行為可以透過實驗引出來,方法是給受試者負面反饋——例如,“根據我們的測試,您的樂於助人和合作精神低於平均水平。”人們不喜歡聽到這樣的判斷,最終會向捐款箱捐款。
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家德拉任·普雷勒茨用他的自我訊號理論解釋了這些發現:特定行為對我的評價通常比行為的實際目標更重要。不止少數人堅持節食是因為他們不想顯得意志薄弱。相反,經驗已經證實,那些確信自己慷慨、聰明或善於交際的人會減少證明這一點的努力。過多的自信會讓人自滿,並加劇他們想象中的自我與真實的自我之間的鴻溝。因此,那些認為自己很瞭解自己的人特別容易比他們想象的更不瞭解自己。

不確定自己是否慷慨的人通常會向慈善事業捐贈更多。圖片來源: Andre Thijssen Getty Images
10.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靈活的,你會做得更好。
人們對自己是誰的理論會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因此,一個人的自我形象很容易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斯坦福大學的卡羅爾·德韋克花費了大量時間研究這種影響。她的結論是:如果我們認為一個特徵是可變的,我們就會更傾向於努力改進它。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認為智商或意志力等特質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改變的和固有的,我們將很少努力去改進它。
在德韋克對學生、男性和女性、父母和教師的研究中,她收集到一個基本原則:具有僵化自我意識的人會糟糕地接受失敗。他們將其視為自己侷限性的證據並害怕它;與此同時,對失敗的恐懼本身會導致失敗。相比之下,那些理解特定才能是可以培養的人會將挫折視為下次做得更好的邀請。因此,德韋克建議採取旨在個人成長的態度。當有疑問時,我們應該假設我們還有更多的東西要學習,並且我們可以進步和發展。
但是,即使是那些具有僵化自我意識的人,他們的性格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是固定的。德國海德堡大學的心理學家安德烈亞斯·施泰默表示,即使人們將自己的優勢描述為完全穩定,他們也傾向於相信自己遲早會克服自己的弱點。如果我們試圖想象幾年後我們的性格會是什麼樣子,我們會傾向於諸如:“冷靜的頭腦和清晰的 focus 仍然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我可能會減少自我懷疑。”
總的來說,我們傾向於將自己的性格視為比實際更靜態,這可能是因為這種評估提供了安全感和方向。我們希望認識到自己的特定特徵和偏好,以便我們能夠採取相應的行動。歸根結底,我們創造的自我形象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的一種安全港灣。
這個故事的寓意是什麼?研究人員表示,自我認知比人們想象的更難獲得。當代心理學從根本上質疑了我們可以客觀和最終地瞭解自己的觀點。它明確指出,自我不是一個“事物”,而是一個不斷適應變化環境的過程。我們如此頻繁地將自己視為比實際更稱職、更道德和更穩定,這一事實有助於我們的適應能力。
